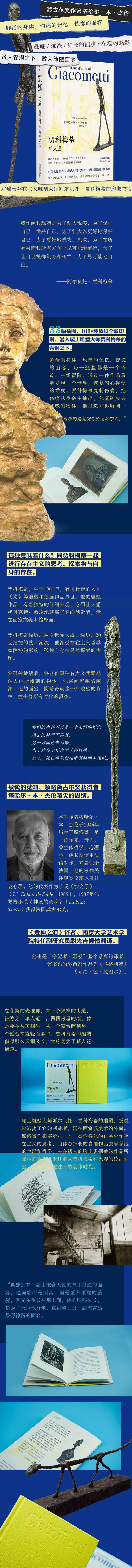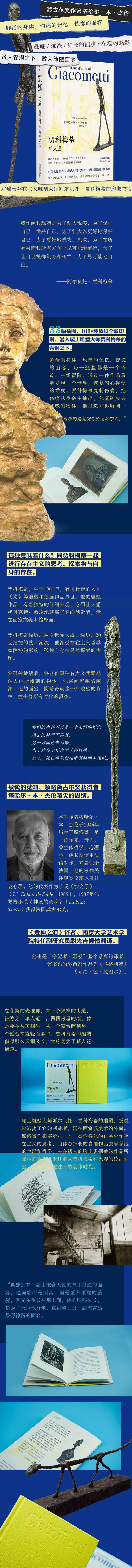在菲斯的麦地那,有一条狭窄的街道,被称为“单人道”。两侧房屋的墙,像是要在头顶相碰。从一个露台跨到另一个露台简直轻而易举。贾科梅蒂的雕塑做得那么又细又长,大约是为了踏入这街道。
瑞士雕塑大师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的雕塑,叛逆地逃离了它的创造者,活在画室或美术馆外面。摩洛哥作家塔哈尔?本?杰伦将他的作品化作存在主义的思考,由体态细长的青铜作品去思考他的生活和哲学,去在活人的脸上识别他的作品所揭示的真实。他还潜入贾科梅蒂在巴黎的凌乱画室,尝试想象他往日的创作时光。
“孤独拥有一副由饱含人性的双手打造的面容。这面容不是面具,而是茎秆 的脑袋,目光在生长在那上面,他的腿那么长,是为了永恒地行走,直到遇见另一副流露出呆愕神情的面容。”
------
我作画和雕塑是为了钻入现实,为了保护自己,滋养自己,为了壮大以 好地保护自己,为了 好地进攻、抓取,为了在所有层面和所有方向上尽可能地前行,为了让自己抵御饥寒和死亡,为了尽可能地自由。——阿尔贝托?贾科梅蒂
? 33幅插图,100g纯质纸全彩印刷,潜入瑞士雕塑大师贾科梅蒂的青铜之下。
——鲜活的身体、灼热的记忆、恍惚的面容,每一张脸都是一个奇迹、一场冒险。通过一件作品重新发现一个世界,恢复内心视觉的维度。贾科梅蒂复制伤痛,把伤痛从生命中抽出,他复制失去呼吸的物体,他打造并拆解同一张脸。
“ 难的是复制你所见的东西。”
? 孤独意味着什么?同贾科梅蒂一起进行存在主义的思考,探索物与自身的存在。
贾科梅蒂,生于1901年,有《行走的人》《狗》等雕塑和绘画作品传世。他的雕塑作品,有着独特的纤细外观,它们让人想起贝克特:叛逆地逃离了它的创造者,活在画室或美术馆外面。
贾科梅蒂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经历过20世纪初的艺术潮流。他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影响,孤独与存在是他探索的主题。
他孤独地活着,将这份孤 力又优雅地注入他所雕刻的物体。他在画室越陷越深,他的画室,阴暗得就像一片浓密的森林,撞击着所有时代的黑夜。
我们的生存不过是一次永恒的死亡
逝去的时间不再有,
另一时间还未到来,
当下就在生死之间无精打采。
总之,死亡与生命在所有时间中相似。
? 敏锐的觉知,领略龚古尔奖获得者塔哈尔?本?杰伦笔尖的思绪。
本书作者塔哈尔?本?杰伦于1944年出生于摩洛哥,是一位作家、诗人,曾主修哲学、心理学。他长期使用法语写作,并居住于法国,他的写作关注现实议题以及社会心理。他的代表作为小说《沙之子》(L’Enfant de Sable,1985),1987年他凭借小说《神圣的夜晚》(La Nuit Sacrée)获得法国龚古尔奖。
?《爱神之泪》译者、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特任副研究员尉光吉倾情翻译。
他也是“守望者?形视”整个系列的译者,该书系的另两部作品为《马格利特》《乔治?德?拉图尔》。
【作者简介】
塔哈尔?本?杰伦(Tahar Ben Jelloun,1944— ),以法语写作并居住于法国的摩洛哥作家,代表作为小说《沙之子》(L’Enfant de Sable,1985),1987年他凭借小说《神圣的夜晚》(La Nuit Sacrée)获得法国龚古尔奖。
【译者简介】
尉光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特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西方文艺理论与法国思想。译有《享受你的症状》《无尽的谈话》《爱神之泪》等,编有《对诗歌的反派》《 的言者》。
单人道
画室访魅记
贾科梅蒂年表
我觉得自己离它们的孤独很近,沉浸于它们不安的傲气。我从它们中滑过,紧贴着墙壁。我将自己视作猫、狗,在茎秆尽头有着极小的脑袋。我迷失了。我冷了。路变暗了。我再也看不见什么。我的手触摸着一块近乎人形的金属长出的腿、背、手指。我明白一种永恒的氛围已降临这街上,用一张无边的沉默的裹尸布覆盖了那些存在。
但它们在这条小巷上做什么?恋人相会于此是为了让彼此的身体在穿行时相抚相触。它们在替一位死者守夜吗?在聆听临终之人的遗言吗?还是在等候饱经幻灭的人到来,用目光传递这阵无边的沉默并献上生命?——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
那里,雕塑沉睡。它们失去了活力,但没有死亡。我的手抚摸青铜,试着认出一张熟悉的面容,一块已知的颈背,一道邻近的目光。我陷入了一阵不安。那不是恐惧,而是太过强烈的惊奇,以及 的确信。孤独拥有一副由饱含人性的双手打造的面容,这面容不是面具,而是茎秆 的脑袋,目光就生长在那上面,而茎秆看起来就像一具脱离一切的躯体,它的腿这么长,是为了永恒地行走,直到遇见另一副流露出呆愕神情的面容,在这熟悉的神情里,孤独不留痕迹地彼此相认。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深渊,来自 、 又毫不妥协的独一伤痛。这就是美。它不是和谐,不是行为和性情的规整,不是对光明和安逸表象的殷勤。我想握住塑造这些存在的手,不是为了让自己获得这些造物身上藏匿的秘密——贾科梅蒂自己也无法获知——而是为了度量它们的厚度和热度,因为它们必定战胜了流亡和痛楚、噪声和恶意。
贝克特总让我想起贾科梅蒂的雕塑:叛逆地逃离了它的创造者,活在画室或美术馆外面。
就这样,那独特的雕塑迈步于无限的时间,摆脱了目光下珍贵的孤独。
从此,不论置身地铁还是火车,不论身处菲斯的麦地那还是马拉喀什,我都寻找着贾科梅蒂的其他雕塑,它们拥有鲜活的身体、灼热的记忆、恍惚的面容。
读到让·热内写的贾科梅蒂时,我明白了,如果美存于这深渊,那是因为“美只源于伤痛。每个人都带着特殊的、各自不同的伤痛,或隐或显,所有人都将它守在心中,当他想离开这个世界感受短暂而深刻的孤独时,就隐退在这伤痛中”。
一张脸就是一个奇迹。每一个相貌都是 的构造,其命运是成为灵魂的镜子。每一副面容都是一段记忆、一场冒险。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长时间专注地打量画室里摆放的这张脸,它就会变成一场冒险:“而冒险,伟大的冒险,就是每天看着某个未知的东西从同一张面孔上浮现。它比全世界所有的旅行还要伟大。”
如果词语擦破他们的面孔或刺入他们的灵魂,乃至严重地扰乱他们,他们会发出抗议。书写变得沉重、艰难,令人局促不安。
“ 难的,”他说,“是复制你所见的东西……你复制的 不是桌子上的水杯,
你复制的是视觉的残余。” 正是通过复制世界,他才看见了世界。只有提取某些对象并复制它们,他才能在世界中到场。
“我作画和雕塑是为了钻入现实,为了保护自己,滋养自己,为了壮大以 好地保护自己,为了 好地进攻、抓取,为了在所有层面和所有方向上尽可能地前行,为了让自己抵御饥寒和死亡,为了尽可能地自由。”
当疯狂让他[阿尔托]陷入可见的恐怖而一动不动时,他写作就是为了不再写作。即便有些句子重叠,不产生任何意义,它们也至少说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一个被生命所驱逐的人无以忍受的苦痛。
他复制杯子。他复制那失去呼吸的物体。他用沉默包裹它,然后把它放在桌子下,放在注定要被遗忘的角落里:只有通过复制,他才知道他从外部的世界里看见了什么。于是,每件作品不过是重新发现了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恢复了内心视觉的维度。
他不止一次打造并拆解同一张脸,因为每一次从贾科梅蒂手中诞生的造物都“细长、透明,就像大火中教堂的彩画玻璃窗,优雅,就像残垣断壁,因失去重量和古老的血脉而受够了苦。但它们高傲果决,如同那些在灌木和灾难不可消除的光芒下,毫无畏惧地参军的人”。(勒内·夏尔)
这是贾科梅蒂治好的一道伤痛:他复制伤痛,把伤痛从生命中抽出,使之成为一段鲜活的记忆。它被造出来,就是为了做证。
这小巧的脑袋,从暮色中挣脱,守夜不眠。它注视我们,威慑我们。贾科梅蒂把它从青铜中提取,因为他从中看见了:这样一个魅像,一道完满的影子,注定是一个在场、一段记忆,厚重,沉默,近乎熟悉。
比莉·哈乐黛的嗓音就是贾科梅蒂的手,它探入青铜内部,凿出一道目光、一声呼唤、一阵缓慢又痛苦的呐喊:发自酒吧里自我耗尽的生命,化为烟气消散的生命,化作烟灰落在钢琴家膝盖上的生命。这是被多少苦厄打破又碾碎的生命所流露的泪水和欲望,这是何其古老、由来已久的记忆发出的嗓音,是被人装上旧船的奴隶发出的嗓音。
正如米歇尔·莱里斯指出:“这间常在他的绘画和图示作品中出现的画室,对他来说,似乎不只是一间实验室:它是他个人和(可以说,他看起来所属的)外壳的一个附肢,一个延伸。”
威廉·福克纳在《蚊群》中描述过一个人,他“面对世间含糊不清的可笑
黑暗,保持 、单纯和永恒”。 我看见了这个人,他就在这儿,也在画室里,被生活击沉,无尽地迈入荒漠的空间,在一块沉重的底座上生根,身上却散发着“赤裸的威严”。
贾科梅蒂对安逸的近乎自然的冷漠,到热内身上,就升级成了敌意,成了对贫困的欲望。钱不是问题。他们都追求本质的东西。尤其是不粉饰表象。
他孤独地活着,他没有把这份孤独传给他的妻子和他的兄弟,而是将其有力又优雅地注入他所雕刻的物体。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出口。他没有别的选择。于是,他在这个地方越陷越深,而这间画室,阴暗得就像一片浓密的森林,撞击着所有时代的黑夜。
我们的生存不过是一次永恒的死亡
逝去的时间不再有,
另一时间还未到来,
当下就在生死之间无精打采。
总之,死亡与生命在所有时间中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