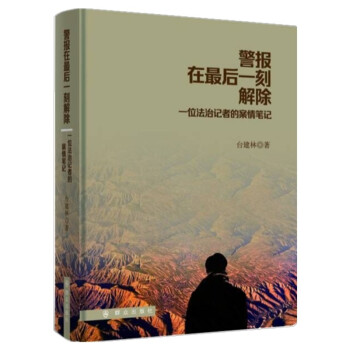
标 签:
本书是一部富有特色的以法治纪实为主要特质的笔记小说。它以一位法治记者的笔触,对曾经亲临现场,或对罪犯的面对面采访的深度报道为基础,以一些大案、要案的侦破过程为素材,重点选择了一些负责侦破的警察作为原型,在展现侦察人员追求正义、和罪犯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还原和剖析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如何成为了一个罪犯的真实故事,让本书多出一种人性视角和人文关怀色彩。同时,作者娴熟地运用富有地域特色的语言,叙事节奏把握恰到好处,故事余韵缭绕,让这部作品具备了较高的文学品位。
该书全景式地展示出了一幅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前现代和现代交错纠缠中的法律生活图卷,为中国法治留下了一段精彩的史话。
“白面”生意
稀软的“少侠”
没费一枪一弹
黑矮个和白高个
小所大案
潜伏者
一只臭袜子
九儿劫
又能跑多久
一口面条
罂粟花的恶
疑心之祸
刘小鱼们在暴雨七月
开在米泉的“陕西发廊”
骗子穷途
“副省长的亲侄子”
曲里拐弯
一
十二年前,卫福祥十八岁上,家里出了一大事。
圆日隐地、天色黑紧的时候,祥子的大大(父亲)荷锄回家,身背后跟着十八岁的祥子和十四岁的大闺女。柴门虚虚地掩着,院里冷冷清清,闻不到往日麦秸、柴草在石头灶里燃出的呛人的甜烟。村里的婶们、姨们,偏偏挤在祥子的家门口。
“你娘昨天去阳村赶集了,不领你妹;你妹哭着闹着跟走了。”
“阳村集市上,你娘穿了一件新新的红袄,紧跟着了一个男的……”
这是1986年的事。1986年的陕西省大荔县沙苑,媳妇、女子被拐骗走了的事可不算稀罕。那是怎样一块地方嘛!黄河在那里拐了个弯,渭河也在那里拐了个弯。两个弯中间,积淀起几千亩、上万亩的沙地,就叫沙苑。起风时,扯天扯地都是黄沙,裹挟得太阳好几日没有颜色;落雨时,遍地沙水横流,路也不见了,刚冒出头的禾苗也被冲刷出根根络络。那里西瓜多,红枣多,花生多,可那年头硬是卖不上价,辜负了满地红红绿绿的宝物;沙地里多的倒是歪歪斜斜的茅草屋——沙苑难留人,留人难留心。
秋忙刚过,枣子、花生赚了点钱,祥子便磨面起灶,烙出十多张锅盔馍,包袱裹了,走陕北,过陕南,河南、山东也掠过一些地方,开始寻找他的亲娘。他写了一张又一张寻人启事,贴在电线杆上,贴在墙壁上,甚至悄悄贴在走州过府的大客车上。地方穷,人就不恋家,走南闯北的就多;村里每每有人外出,祥子都咬咬牙,去村头小店买一盒带过滤嘴硬盒烟,求人家带着探问他娘和妹的消息。都是有骨肉血亲的,有的人在心里感念祥子的这一番亲情,便坚辞不收他的烟,出了门却尽心探问。
整整一年之后,1987年,村里一人到山东济宁给机井买机具,想起每年春夏种收西瓜时,沙苑人都要在山东单县请帮工。内中一个叫郭宝发的,年年去沙苑,今年却没露面,便多了一心,拐到单县毛庄乡刘草房村郭家。他在村口,撞见了祥子的娘。
娘是被人拐带走的!娘,娘!你不识字,可你不晓得自己的家在哪条路上?不晓得自己的儿子、闺女在等着你?
二
祥子心里一时想娘的不是,一时又念娘的苦处。终于决定,还是要去一趟山东,看上娘和妹一眼。最好,能把她们接回家。
这事肯定得动公安。祥子摸进了官池派出所的门。等他哭完,诉完,警察们稍作商议,转日派出两人,与祥子一起往山东去了。
从黄河头到黄河尾,千里的路程不歇脚地赶,一众人赶到毛庄乡公安派出所。等两省公安交接完公事,毛庄的所长,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警察苦兮兮地笑道:“又是一桩拐骗案!那个刘草房村,是块三省不管的地方,也是穷,群众的法律意识真的太薄弱了!”
随警察进村时,祥子的眼光就有点挑剔:地是平地,可是泛碱,种粮、种棉,产量不会很大。郭宝发的家,也不过是三间草房。中间与左首一间住人,右首一间还圈着牲口,满屋是畜腥味——这条件,与沙苑自个家还赶不上哩!
可是,娘不在,妹不在,郭宝发也不在。在家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郭宝发的老大大。
老汉一听问起郭宝发从陕拐妇女的事,一颗花白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哪里?哪带啦?我没见呀!宝发就没回来么!”
个把月过去,祥子又和四叔一块启程。四叔在部队服过役,有见识,有胆子。到了单县,留下祥子,他一人闯进刘草房村,说是收银元的,东走西串。顷刻与村里人厮混熟了,哄出郭宝发在村东二十里处一个砖窑干活的消息。四叔急找了祥子,风一般到砖窑。人说郭宝发刚走,带着“西边来的媳妇”和一个小闺女。
祥子和四叔昼伏夜出,在四乡八村排查了十多天,带来的盘缠用尽了,娘和妹还是没影,后生心酸得流下几行眼泪。
转年冬天,枣子和花生卖完后,祥子又出现在刘草房村。郭老汉不依了,凶神恶煞样堵住柴草门:“你再来,我就砸断你的腿!”
傍晚时分,下雪了。大朵大朵的雪花飘飘摇摇地砸下来,很快罩白了巷道。有人从巷道急急走过,发现郭宝发家的草门前立了根雪柱,心疑了一下,绕过去细看,却是陕西那个来寻娘的后生,面对郭家跪着,成了雪人,成了雪柱。刘草房村那人心里一热一酸,上前狠劲擂开郭家房门。
洗过,喝罢,郭老汉端来一盘玉米面窝窝头,叫祥子吃。祥子却一眼看见案板上擀了半截的面条。那一层摞一层宝塔似的形状,那擀杖的放法,不是娘擀的又是哪个?祥子“扑通”一声跪在当堂,一串哭声一串泪:“我也不吃你的饭,你放娘出来吧!”
郭老汉眼里也潮潮的:“造孽哩!……叫宝发刚刚拉走了!这一去,没有一年半载是见不上了……”
三
1998年春节,正月十五刚过,祥子和大妹登上了赴鲁列车。
车上,一对年轻人相对无语。十二年过去了,大妹已经出嫁,祥子也已娶妻生子。十二年来,他们的大大几乎没有一日不低勾着头。地里的、村里的,一切一切的事务,都撇给了祥子。大大完全叫媳子被拐走的不幸给压垮了。祥子丧葬了爷、奶和外爷,又将已经瘫痪的外婆接到家里,与媳子一道精心侍候。祥子的孝心德行,在沙苑十乡八村响得摇了铃。老人们教诲子孙,往往要拿“看人家祥子”的话开头。风霜雨雪中,祥子这一株沙枣树早早地拔起腰杆,硬朗朗地撑起一片天空。十二年来,娘的音容笑貌也没有一日不在祥子的脑海里翻腾,叫他怕见晴空满月,怕听大年炮仗。几乎年年秋后,稍有余钱,祥子都要跑一趟山东,跑一趟刘草房村,期待有那么一次正好能撞见他娘。然而,命运总是叫他失望。他每次撞见的,总是那个愈加衰老的郭老汉。今年,他要换个法子,在大过年时去。难道郭宝发连年都不在家里过?
天色黑净的时候,刘草房村近在眼前了。还是那三间草房,麻纸窗上还是映着煤油灯昏黄的光亮;窗里传出来的,是一片喧哗热闹的声音。掀开房门的那一瞬间,祥子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屋子正中,摆一张方桌。桌子正中,摆一盏油灯;油灯四周,是四个男人,各人捏一把骨牌。此刻,他们都有些惊诧地望着祥子和大妹。其中一个男人的椅子背后,立着个苍老妇人。
那眉眼,那神态,不是娘,又是哪个?一声“娘”,在祥子胸膛里膨胀!他耳朵里满世界都是喊“娘”的声音,可他就是张不开嘴。
娘走近来,走近来,细细端详这个后生、这个闺女,嗓音颤了几颤,问:“闺女,你俩找谁?”
大妹“哇”的一声吼哭起来:“娘啊!”三人抱头,哭作一团。
十二年的骨肉离散,十二年的苦楚,十二年的泪水像是要在这一刻流完。哭声悲悲切切,压得豆大的油灯火苗愈发地小。
不知什么时候,四个男人中走了三个。剩下的这个,就是郭宝发无疑了。哭声止住,一片沉寂。郭宝发强作坦然,叮当当摆上来两碟凉菜、一瓶烧酒,要招待祥子和大妹。祥子看也不看桌子。
他娘慌了,急急拉住祥子胳膊:“孩子,去陪一下,啊?”
郭宝发喝酒是高手,不用杯,不用盏,几口便将一瓶酒全灌进自个肚里。这一斤白酒落肚,闹得他不得安生。他踅过来,踅过去,摇摇晃晃地拖开方桌。猛地一下跪在祥子脚下,左手抽自己一个耳光,右手又抽一个,嘶嘶哑哑地道:“……我不是人!不是人!你找你娘十二年。我知道,我知道……这一回,你们带你娘走吧,走吧……要走,夜里就走!别等天亮。我本家人多,十一个侄子哩,咋都能打折你们的腿……”他说着,哭着,半句话含在嘴里,竟呼呼地打起鼾声。
祥子立起身,挽住娘,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停脚。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见到小妹。娘说,小妹去了邻村一个小姐妹家。只好硬等。
“郭老汉呢?”祥子想起那个凶巴巴的老汉。娘的嗓门本来就低,这时又压了压,细如游丝:“叫他儿打死了!他儿喝醉了酒,打得老汉鼻子、嘴里都是血。老汉气不过,喝农药死了……那人真是凶啊,一喝就是一瓶酒,蹲在地头,逼我和你小妹干活,比地主还狠……”大妹就哭:“小妹长啥样了?”
娘也哭:“能啥样?一天学也没让上,就是扣住娃给他干活。在砖窑上给人脱土坯,工资全叫他拿走。晚上还要翻娃的衣兜,怕娃藏钱……衣衫一穿就是五六年,糟得一拽就是道大口子。他就不给娃买新的……”
大妹揉了一下眼窝:“你走后不多时,村上给家里分了十亩沙地。我哥全给推平,养成好地;又打下一眼机井,买回一辆蹦蹦车;他埋了几个老人,还自己结了婚,嫂子也贤惠,村里人都高看一眼哩。……这十多年,娘就不想回沙苑?”
娘给祥子、大妹挨个抹眼泪,自己的泪却断了线地淌着:“想哩,想哩,可咋回呀么?娘不识字,可怜你妹也不识字,坐哪趟车都搞不清。再说,那人又看得紧,从不给我俩一分钱。这些年转来转去,去年冬天才找的这个窝……”
“跟我们走吧?”大妹哀求道。
娘犹疑了半晌,问:“……你大大……”
这才是那最关键的一句。
大妹说:“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啥?这次来,大大直把我们送出村口……”
一句话,一行泪,娘仨个哭了说,说了哭,像是过了几世,又像是才几分钟。正月十六的太阳,从刘草房村的草房后边升起来了。天地间一片灿烂。
小妹天亮前没有回来。她回来时,哥、姐已经在一百里外,坐上了返陕的列车。
郭宝发醒来后,将祥子娘圈进草房。他闩紧柴门,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又将粪叉、镰刀和切菜刀压在枕头下。村里人喊他出去打牌,他也不去,隔窗吼说:“陕西那小子走了,我得防够他一百天。这一百天不出乱子就罢;一出,肯定是大事!”
四
3月28日子夜,刘草房村的人歇了,灯熄了。两辆小面包车开进来,调过头,车尾对着村子,车门大开,跳下来一个黑影,两个黑影——一共十三个黑影。有人在那里压着嗓子调遣:谁谁守车,谁把住村口,谁谁进屋。交代停当,十三个黑影眨眼间散失在黑暗里。
进村后,几个黑影径直飘到一家门口,又分作两拨前后把定,才叫门:“有人吗?”
屋里豆大的煤油灯陡然亮起,有妇女问:“干啥的?”
屋外人道:“查户口。”
门开处,几个人齐齐拥进房子。最前头一人握着本工作证,让男主人看过。果真是毛庄公安派出所的民警。民警眼瞅住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一个十六七岁的闺女,问:“有身份证吗?”二人摇头。民警就挟着母女二人的胳膊往门外走。见那男人发愣,民警边走边回头解释:“没多大事,到派出所补个证去。”
男人撵出门外,民警和母女二人早就像风一样不见了踪影。
村口车旁,一个黑影抢迎上来几步,与母女二人撞出热热的呼叫。
正月,祥子从山东刘草房村返回陕西沙苑后,早也想着娘和妹,晚也想着娘和妹。刘草房村离最近的车站还有一百里路哩,他接了娘和妹,如何跑过这一段距离?他又怎样将娘和妹接出村子?一个个难题,一苗苗心火,烧得祥子嘴唇起了一串串燎泡。
一个清早,祥子终于坐在大荔县公安局官池派出所的报案室里。案情,从张凤祥所长那里急报到县局刘载一局长案头。
公安民警的心,被百姓的苦情紧紧揪住。一套解救方案出台了。3月28日下午,陕西民警赶到山东毛庄;子夜,毛庄派出所年轻的所长带着两省民警组成的解救小组出发了。
车回沙苑,已是29日深夜。祥子长长地吁出一口气。东天上,一丝上弦月挤在满天的星星中。月是残月,又被枣树生铁似的枝杈遮得疏疏离离。祥子的心里,一个煎熬了他十二年的梦,却渐渐变得浑圆。
开 本:32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