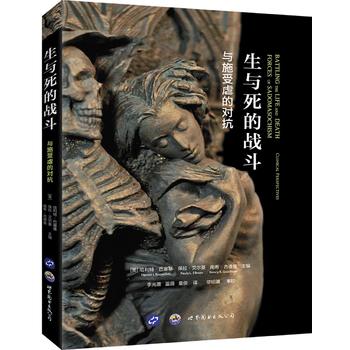
作 者:(美)哈利特·巴塞基,(美)保拉·艾尔曼,南希·古德曼
译 者:李光芸,蓝薇,童俊
出 版 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7年05月
定 价:58.00
I S B N :9787519225957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心理学 > 心理学理论与研究
标 签:精神分析 心理学 心理学理论与研究
哈利特·巴塞基(Harriet I. Basseches),哲学博士,曾担任独立精神分析协会联盟(CIPS)主席。
美国职业心理学委员会(ABPP)成员,国际精神分析协会(FIPA)会员,当代弗洛伊德学会(CFS)和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培训与督导分析师,CFS终身教员。
保拉·艾尔曼(Paula L. Ellman),哲学博士,华盛顿大学职业心理学中心临床心理学副教授。
美国职业心理学委员会(ABPP)成员,国际精神分析协会(FIPA)会员,当代弗洛伊德学会(CFS)和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培训与督导分析师,CFS终身教员、华盛顿项目主管。
南希·古德曼(Nancy R. Goodman),哲学博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FIPA)会员,当代弗洛伊德学会(CFS)华盛顿项目和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培训与督导分析师。CIPS“活现研讨小组”主持人,CFS终身教员。
A先生的原始超我:施虐复仇幻想、激发及随后的受虐懊悔
——来自理查德?瑞驰巴特的案例
很难回想起十五年前和A先生一起工作时的感受,要描述当时的治疗也并不容易。A先生可以极度乏味并持续重复,这让我在他躺在沙发上时不得不时常转动眼睛。实际上,开始那些年的几乎每一次治疗都是以A先生的同一套说辞开始:他如何不想接受治疗、我如何试图伤害他、他如何不能讲出新的东西,以及他如何想离开。在治疗的早期,每一次治疗都必须先有四十分钟的指责,之后才略有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指责的时间逐渐缩短为半个小时,到十五分钟,再到十分钟,最后只剩下他对仍然来见我感到不舒服的一两句抱怨。也是在早期治疗的时候,他还容易焦虑,经常在治疗结束时威胁想自杀(他在父母房屋的地下室里装了一个套索,他经常躲在那里,连续几个小时盯着他养在一个巨大水箱里的鱼),他也经常乞求我,恳求我“让他走”,放弃他。那时我刚开始进行精神分析工作,接手任何躺椅上的案例都让我兴奋不已,我想我也获益于这种天真。尽管他接近精神病的某些东西也会冲击到更有经验的分析师(我作为候选人向一个分析师报案例,他告诉我A先生“病得很严重”,不断地提醒我这样的治疗很难把控),我仍然和他艰难地往前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乏味复乏味。在多年的治疗以后,我惊讶地意识到,这个边缘的、自我放逐的人已经改变了他的生活,结了婚,变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有冲突但还是很慈爱,对自己的情感和恐惧也有了一定的理解。
但在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并不乐观。A先生26岁,说话和表达情感时绷得比鼓还紧。他驼着背,表情呆板,给人一种既不想让人注意也不想注意别人的印象。当他坐在候诊室的椅子上时,看起来就像纽约地铁上你本能地想离得远一点的那种人。他流露出对他人的不信任,全身上下都散发出“离我远点,别和我讲话”的气息。实际上,在十年的时间里,A先生都害怕去候诊室,更愿意准点从车里直接进入治疗室。他避免和街上遇见的任何人及其他病人有眼神接触。因此,他也看不到环境中很多明显的东西。他花了十五年时间才发现我治疗椅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虎皮百合的水彩画,几乎每个进来的人首先就会注意到这幅画。这对他来说是个没用的信息,每次他走进来,他会侧着看一下我,再走到躺椅那里。
由于这个原因,A先生提供不了他自己的信息,因为他完全不记得自己的幼年。他的记忆从青春期开始,这些记忆都是创伤性的。就好像从有象征意义的犹太成人礼起,A先生就开始了离开文明世界而不是成长为有责任的男人的旅程,他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发展的。青春期在犹太成人礼后来临,A先生说他之前有的都是“正常”的朋友(尽管实际上他从来没和他们讲过话),自那时起他换了新朋友,和一个施虐的男孩走得很近,他理想化这个男孩,总是追随他。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但A先生相信其中一个明显原因是,到青春期后他的乳房变大了,让他显得很女性化,这让他意识到正常孩子是不会和他一起玩的。他从那时起开始避免脱上衣,拒绝在家里的游泳池游泳,彻底放弃了游泳的爱好,换了朋友。在六年的治疗里他一直相信他的乳房很大。在十四年后他才能对我说,“我以前怎么会相信自己长了乳房?”
另一个导致了成年仪式之后这些变化的原因是,A先生认为他无法用“正常”即爱或接受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他认为这个世界残酷而恐怖,因此无法理解,即使他的家庭也是如此。他变得扭曲了。出于这个原因,他在自己和世界的严酷中得到了不同寻常的施虐愉悦。世界的“正常”方式——任何相信世界充满善意的观点——都会被认为是愚蠢的而被鄙视。
在我进一步讲述这些历史之前,我不想留下A先生能直接讲述他历史的印象。相反,他在多年之内都只能断断续续地讲述。因为感到难堪或感觉他的行为令人厌恶,多年以来,他会向我遗漏过去生活中他能意识到的关键事件。接着,当他内心的某部分被触动、当他感觉安全时,他才会说起他有很重要的事想要告诉我,但他不能这么做。通常在几个月后,他会告诉我一部分内容,但对关键信息绝口不提。有时我能在他明显不完整的故事中提炼出其中的关键内容,有时却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一无所获。这种带着戏弄的隐瞒不仅是种防御,更是一种施虐的攻击,策划——虽然有时是潜意识的——误导并挫败我。
这个过程里涉及很多事件,大部分与性有关。A先生最终告诉我他在青春期时被母亲的引诱“缠住”(这是我的说法)。当他开始治疗时,他用崇敬和敬畏的方式描述母亲,她是个强势的家长,拥有自己的生意。他认为父亲软弱,对他不屑一顾。到了青春期,父母在家里的角色显然和他儿童期不同了:以前总是母亲做家务,但现在几乎完全不做了。父亲不再工作那么久,承包了做饭的任务。典型的事件是,A先生青春期时,母亲总是穿着内衣吃饭,饭桌是玻璃的,A先生变得强迫性地去看她的胯部。吃饭结束后,他对她的兴趣更加深了,她把椅子往后一推,点上一支烟来放松,双腿交叉。到了晚上,A先生也会去母亲的卧室,当她给他辅导功课时,她穿着内衣躺在那里,他则坐在床上。母亲曾经是个小学老师,但辅导过程让A先生感觉复杂。他可以不去看她,但一直怀疑她究竟会暴露到什么程度。他多少有点相信她希望他看她。说到这一点,A先生学习有困难,他看起来有某种程度的阅读障碍——因此母亲确实帮了他很多。这个学习困难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母亲努力让知识性欲化而被创造出来的,而不仅仅是加剧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完全明确过。然而可以这么说,在治疗的后期,A先生能够毫无障碍地学习,他的工作表现和他在工作中对他人福利的责任有赖于阅读和理解能力的提高。
当父母不在家时,A先生会进入他们的卧室,翻出母亲的镶边内衣,穿上她的内裤。他感到极度兴奋并会手淫。有时他会拿走母亲的内衣去处理,因为他害怕被发现他射精到了内衣上。有时他只为了放回母亲的内衣去父母的房间。他认为母亲对此事有所察觉,毕竟她的内衣会时不时地消失。
通常在晚饭和他做完作业后,父母会回卧室,接着能闻到很强的气味,很显然他们在吸大麻。这个过程激怒了A先生:他感觉母亲让他激发起拥有她的想法,却和父亲一起走进卧室,把他关在了门外。有一次,A先生发现后院里种了一株大麻。实际上,A先生从青春期开始就沉溺于大麻。他在贩毒,但从来不告诉父母。他吸得非常厉害,多年来每天都吸,所以在治疗的早期,他相信是吸毒导致的大脑损伤让他无法回忆起童年期的经历。他在快成年时因为持有大麻被捕并被判缓刑。就在那时,那株大麻从后院消失了。
他和朋友拉尔夫的行为反应了他强烈的自我憎恨、危险性和施受虐。拉尔夫、A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常常聚在拉尔夫家吸大麻。拉尔夫是这伙人的头目,A先生对他极度崇拜。他对拉尔夫和新结交的朋友隐瞒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的姓不是典型的犹太姓氏),并和他们一起反犹。实际上,在治疗初期,A先生因为身为犹太人而羞愧。当他们一起坐在拉尔夫的摩托车上,他在拉尔夫身后体验到一种特殊的快乐和恐惧,拉尔夫的车速常常极快,非常危险。那时他会既兴奋又害怕。此外,拉尔夫会虐待动物,A先生会充当帮凶,或者兴致勃勃地旁观,印象最深的是把鸡放到火上烤。A先生在那时认为这很好玩,在治疗时一边描述鸡的样子一边忍不住发笑。有一次,在和拉尔夫及朋友们吸完大麻又喝了酒之后,A先生大醉至不省人事。不清楚A先生是不是在那时被拉尔夫性侵的,他从饲养动物里回忆起来的大部分内容都和性有关。A先生心中还有另一个亲密朋友——他的狗,他对它非常依恋,绝不会伤害它。在他的移情中,A先生会把我看成这条狗。在他刚开始治疗时,这个童年时期的宠物已经去世了,父母又养了一条狗。尽管新来的是只母狗,有命名权的A先生却给它起了一个男性名字,父母也同意了。
在青春期早期,母亲规律地带他去看一个牙医,他和这个牙医也有过一些体验,他在治疗早期经常对此加以描述。当他坐在治疗椅上时,牙医会把工具放到他的膝盖上。A先生发现自己会在感觉疼痛又不得不张开嘴时兴奋起来。每次牙医取工具时,A先生都会感觉到他碰到了自己的阴茎。A先生没有把这些告诉母亲,她依然带他去看牙医,他只能一次次地返回那里。有一次,他被自己的射精吓坏了。作为一个年轻的成年人,他和理发师也有过相关的经历。他显然害怕去见这个理发师,因为他发现自己又兴奋了。他认为他的卷发很丑(母亲是直发),坚持要弄直,再从中间分开。他光顾多年的理发师是个男人,也反犹,他在理发师面前假装不是犹太人。另外,他还假装已婚,这样理发师就不会把他误认为同性恋。和理发师预约和去理发都让他焦虑,因为他害怕理发师会像以前的牙医一样引诱他。A先生会不断拖延,对此有强迫性的忧虑。
事实上,任何新的活动都会让A先生焦虑。当他考虑要做点新尝试时,他会感觉恶心。更具体地说,他无法接受(有时作为我让他进行观察的结果)任何被攻击,以及性欲所激发的感受。这些都让他开始无法控制地恶心。此外,无论是期望还是体验这样的快乐,通常会因随后出现的严重偏头疼而冷却下去。尽管A先生表达了想和女性发展关系的愿望,但他在治疗开始时能记得的唯一性关系是和他非常喜欢的堂妹。在他青春期时,他们在祖父母佛罗里达的家里试图做爱,后来好像被打断了,不过祖父并没有发现什么。尽管A先生非常爱她,这个经历让A先生走了出来,哪怕对她爱意满满,但乱伦愿望仍然让他感到不适。
尽管他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困惑,对性和施受虐的欲望感到恐惧,但A先生最渴望的还是和一个女人建立满意的关系并结婚,他乞求我的也正是希望我能帮他做到这一点。当然,最终约会的过程也会像其他事情一样充满了焦虑。想到女人的阴道让A先生感到厌恶,一提到这个他就想呕吐。他无法忍受看见女性的阴道,实际上,为了避免这样做,在第一次结婚时他会因为害怕而想吐。出于这个原因,他几乎无法亲吻或碰触女人。亲吻也是恶心的体验。同时,在结婚后,他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在送别时会“无意地”亲朋友妻子的嘴唇。实际上,在他自己的婚礼上,当母亲亲他时,他们都亲的是对方的嘴唇,尽管这让他心烦。我认为在他还是小孩时,母亲就习惯这样亲他。
A先生恨他的妹妹。在整个童年时代,他感觉她独占了所有的关注。她总是喋喋不休地讲个不停。A先生很安静。她会突然尖叫来让母亲回应,A先生却不会抗议母亲的行为。母亲和女儿不断喊叫,结果是A先生把自己隔离在自己的房间里。A先生害怕妹妹会发疯,也对母亲有同样的担心。同时,A先生忌妒在妹妹是个孩子时就敢和母亲顶嘴,因为尽管妹妹和母亲曾经相互敌视,但妹妹成年后成了母亲最好的朋友,他为此感到困惑(并伴随更深的嫉妒)。他回忆起十多岁时,妹妹会带朋友回家,而他没有,这也激发了他的嫉妒。A先生还能想起他甚至还是个孩子时,吃饭时会拒绝任何原本是给妹妹准备的食物,哪怕是同一种食物。他希望他的盘子只为他一个人而准备。
母亲有很明显的歇斯底里,尽管在治疗开始时A先生很难识别出其问题的严重程度。她生下A先生时只有十几岁,在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个笨拙的母亲。尽管她做起生意来很能干,但只要丈夫因为生意晚上无法回家,她就会变得歇斯底里。她会不断给丈夫打电话才能消除疑虑。只要可能,她的丈夫会从非常远的地方开车回来(通常是几百英里),第二天一大早又开车去参加商业会议,而不是待在旅馆里过夜。无论何时她感到焦虑,她的丈夫都会立刻赶去陪她,照顾她又哭又叫的发作。她的歇斯底里占据了整个家庭的注意力。A先生感到他的需要不但被母亲遗忘了,也被父亲因为想照顾母亲而遗忘了。在A先生的记忆中,父亲从来都没有因为母亲的歇斯底里而指责过她。
然而,尽管母亲歇斯底里又自我卷入,A先生仍然觉得母亲比父亲更关注他。父亲从来不谈论情感,并苛求细节,对A先生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也从不带他外出。相反,母亲喜欢运动,父亲对运动一无所知,显然对此也毫不在乎。因此,母亲在A先生小时候带他去打棒球,为他加油,和他谈论体育。她会打开电视看体育比赛。虽然A先生并没有体育天分,但他在运动时感觉到了在其他地方从未体验过的完整感和能力感。不幸的是,在我们开始治疗时(尽管从那以后开始改变),因为他太孤立了,以至于无法参加任何活动,他只要见到陌生人就感到焦虑。
A先生非常惧怕母亲,同时又极度地认同她。他认为她强大而让人害怕。她人格化了他的超我,如果没有在自己内心听到母亲的反对,他就无法与人互动。他觉得唯一能在情感上接近的人只有母亲,他们有排他的、性欲化的关系。因此,就像试图接近母亲以外的其他女人一样,任何想接近我的努力都充满了危险,交普通朋友则安全多了。一方面,他害怕如果他这样做,母亲会勃然大怒并不再保护他;另一方面,这么做让他感觉背叛了母亲。在某个层面上,A先生的力量来自他相信母亲在性方面更青睐他而不是他软弱的父亲。同时,当A先生变得焦虑时,他表现得和母亲一摸一样:歇斯底里,忘了他世界里的其他人。他非常害怕焦虑,因此避免做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或是尽可能地拖延。
可以想象,A先生的孤立也非常严重,因为他会经常嫉妒并和潜在的男性朋友竞争,也因为他对遇见任何女人可能产生的性欲而感到害怕。自从结婚以后,当他遇到喜欢的女人时,他会害怕自己会因为对她的性幻想而失控,从而躲避她。如果遇到有妻子或女朋友的男人,他会立刻意识到自己在无声地贬损对方,指责对方的谋生能力或对妻子的疏忽或为人父的资格,以此来幻想他会取代这个男人,成为那个妻子更好的丈夫(在某个层面上,他对母亲的幻想也是如此)。由于投射的结果,他的性愿望、他的竞争,以及他对刚认识的人的敌意,令他变得极度焦虑,因此他经常拒绝出门,或者就算出门,他也无法参加社交往来并发展新的关系。在这一点上,需要指出A先生无法掌握社交中的一些微妙之处。他经常把别人的玩笑理解为对自己的敌意;经常完全不能理解他人的话语,同时,他会全然不觉地讲一些极度冒犯的话,却以为这是在开玩笑。此外,我也需要说明的是,A先生意识不到他有严重的近音词误用,在他试图讲方言时经常发生,这和他通常正式而生硬的讲话方式完全相反。在这一点上,我观察到A先生像一个害怕内在的欲望无法控制的人(像一个紧张的醉汉),有时说话极度冒失却并非本意如此,接下来却是不同寻常的严肃,把接触他人的任何场合都看成雷区,无论对方是陌生人、朋友还是他爱的人。
施受虐意念、激发、报复与懊悔
A先生的背景材料并不足以让人他的施受虐幻想做好准备,这弥漫在他的想法以及和我的互动中。当他感到足够安全时,便不再啰嗦而乏味。这些幻想十分残酷,揭示它们的最好办法可能是:在进一步讨论治疗过程前,我再提供一些不同治疗的片段。例如,他相信他五岁的女儿会看见他的阴茎,接着他幻想她吮吸他的阴茎,然后她会死掉(部分是因为这样她就没有办法告诉其他人)。随后他希望我惩罚他,用五个多小时的时间慢慢把他打死,然后我会因为良心的谴责而自杀。他希望我永远不要救他,因为他很坏。他想说,“去你妈的。”或者当他在聚会上被一个丈夫也在场的漂亮女人迷住时,他会联想到他的母亲。治疗中,他想勒住她的脖子,在众人面前把她举起来的场景让他变得兴奋。他的愿望是要报复,要母亲因为羞辱他而遭受痛苦,这让他兴奋。有一次,他考虑报复母亲,在治疗进行很久后告诉我,他十多岁时在母亲的卧室发现了震动器。他希望那是卷发棒,用他“太烫”的阴茎插入她的阴道烙伤她,以此阻止她和父亲性交, “烧伤她,给她打烙印”。他相信她会因为疼痛而哭出来,接着他也想象对我这么做。
一个月后,经过多次治疗,他意识到我“是个友善的人”,我开始不被他的幻想所影响,这激怒了他,他不断地想起在童年期受虐的朋友拉尔夫。他想吸拉尔夫的阴茎,他被他吸引。他想让我变成像拉尔夫那样“刻薄的混蛋”。接着,他想让自己变得“邪恶而失败,是最好的失败者”。他幻想他变得兴奋起来,全身赤裸,把我拷在椅子上。他会用阴茎摩擦我的胸膛,射精到我身上。我会担心他把阴茎放到我嘴里,我会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下一次的治疗里,他做了进一步的描述:他会割下我的睾丸和阴茎,像香肠和豆子一样吃掉,而我会和他坐在桌旁,被割了阴茎,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对此哈哈大笑。
在许多次这样的治疗里,情况会太快地反转,他的施虐会转换为同等残酷的自我惩罚的受虐,这阻碍了针对他感受的工作。后来还有一次,A先生非常心烦,希望能理解为什么他会因为这可怕的想法而兴奋。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两件事变得清楚起来——他需要他的阴茎能得到有效的承认,他的男性身份能被接受(因为父母对他进行了心理上的阉割),而且他不情愿放弃施受虐的激发所带来的兴奋(尽管他也憎恨它)。实际上,他为这些激发的兴奋时刻而活。对我来说,在移情中十分重要的是,对他的男性身份而不非施受虐进行认同。
治疗过程
接下来,我将使用第十二年的一次治疗来举例说明A先生的愿望是如何原始,他的超我是如何严厉。在这次治疗里他试着谈论结交的一个男性朋友,实际上是一个父亲般的叔叔。尽管A先生小时候住得离这个叔叔和他的妻子并不远,但他的父母从来没有拜访过他们,也没有邀请过他们做客。很多年后的现在,A先生正努力和这个叔叔做朋友,这个叔叔和他的妻子先对他表达了兴趣。这对A先生来说并不容易,因为他感到他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并不赞同,实际上叔叔婶婶比他的父母更能接受他的孩子们。虽然这加大了他的困难,但事实上看起来还是容易的。因此,A先生对他喜欢叔叔而感到内疚。当叔叔提议他们一起去钓鱼(钓鱼是他和父亲为数不多的活动之一,但他们只去过一次,后来父亲也没有再带他去过),他就变得很慌张。我不知道的是,当叔叔告诉A先生他会教他一直想学的假饵钓鱼时,他对接受这个提议的恐惧被加重了。
治疗以他继续谈论如何害怕和叔叔一起出去并享受其中开始,他害怕自己会因此出现严重的偏头痛——就像和其他男性朋友出去时一样。他随后幻想叔叔会强奸他,强迫他肛交,接着他幻想我也会这么对他,因为我的阴茎很大,所以他会受伤。我想知道他为什么需要认为肛交只会让他痛苦,或者我的阴茎很大。他接着想象我会拿着他的阴茎,这让他感到厌恶。他说他会射精,射得非常远,击中他头上挂着的那幅画,我因此不得不把赶他出去。他又想象他逼迫我肛交。就在这时,他开始指责我,说这对他没有帮助,问为什么我会让他这么做。他威胁要在治疗后到车前去自杀。或者他也可以简单地取消和叔叔的计划。他可能不得不取消,因为他现在想象着叔叔教他怎么撒线时会碰到他的手,会站在他后面。他坚持说我会赶他出去。我问他,“为什么?”他坚信他做了冒犯我的事,坚信我会伤害他。我指出这是他的幻想,“我为什么会被冒犯?”我告诉他,他没有做任何伤害我的事,这只是一个愿望,一个幻想。他坚信如果他在治疗室里射精就会被我赶走。我问他,“为什么?”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清晰地表达施受虐的想法并感到焦虑。因此,当他继续这么说,那么就算不是现在,我迟早也会受够他,会摆脱他。我告诉他,很显然他并不想修通这些想法并从中解脱,他更愿意维持这些想法,让自己不交男性朋友,始终把自己看成受害者。(我之前做过这样的解释,但不是完全一致,也不是在建立友谊的愿望如此强烈时立即进行解释——毕竟他一直避免友谊)。在第二周的治疗时,他说在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的身体并没有他认为的那么不好,这让他感到惊讶。他说,“我以前怎么会相信自己长了乳房?”接着,他花了很长时间讲他的叔叔,想象自己会因为他的拥抱而兴奋。我向他解释,他的幻想之下潜藏着他的渴望,他希望人们注意到他的勃起,他希望我赞美他的勃起。他这样的需要源于母亲只穿内衣出现在他的面前,她否认了他拥有阴茎,他的父亲也是如此。他希望我承认他拥有阴茎。他沉默了,泪水布满脸庞。过了一会儿,他能够说话了,他说他想要一个我这样的父亲。
六个月后,他的母亲突然因为癌症去世。过程很可怕,从始至终他的母亲都非常愤怒和歇斯底里,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否认自己要死了。但她的死亡也带了奇怪的积极影响,在最初的震惊和哀伤之后,A先生从全能的母亲形象中解脱出来了。同时,母亲的去世带来了另一个失望:A先生曾经幻想,在母亲走后,父亲会和他面对他们共同的丧失,父亲会更亲近他。然而,父亲仍然像以前一样疏远他。因此,A先生感到更依赖我了。有一次,我因为短暂的休息而取消了两次治疗,他对此非常愤怒。他说我的离开对他不公平,接着又说:我有一个精神病的母亲,我和父亲讲不了一句话,我的妹妹很古怪,所以我总是对动物很依恋。(他笑了)我希望你会带只小狗回来。我永远都不会对你有亲密的感觉,因为我对受伤和失望受够了。现在我把你当作一只长尾巴的恐龙。我想养只蜥蜴当宠物。(他又笑了)
我常常觉得连我的妻子都不算我的朋友。我总是觉得我并没有真正了解你,我也不想你了解我。我从来都不了解我的妻子和孩子。因为我的求胜心,我和任何人都没有平等地相处过。在这里好像也是如此,一种消遣,里面的关系有问题,只不过是和我的分析师。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改变。
……
装 帧:平装
页 数:312
版 次:第1版
开 本:大16开
纸 张:纯质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