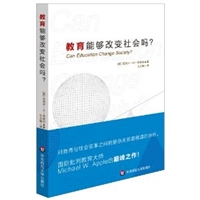
作 者: Michael W. Apple
译 者:王占魁
出 版 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03月
定 价:32.00
I S B N :9787567515246
所属分类: 教育学习 > 教育学
标 签:教育 社会科学
对于教育在生产不平等方面的作用,左派和右派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然而,不论是主张让教育重建正在消逝的一切,还是强调让教育彻底改变现行社会的一切,能够为双方都认同的一点是:教育能够并且应当对社会发挥重要作用。1932年,激进派教育家乔治 康茨以最简洁的形式提出“学校敢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吗?”这样一个问题,它对当时所有参与和实际领导社会重建运动的教育家提出了质疑。70年后,通过把这一问题与少数群体中具有同样影响力的作品相比较,著名的教育家、作家和活动家迈克尔 阿普尔重温了康茨这部标志性的著作,并再次提出了这个看似简单的有关教育是否真地有能力改变社会的问题。
阿普尔(Michael W. Apple),1942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1966至1970年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师从著名的教育哲学家乔纳斯 索尔蒂斯(Jonas F. Soltis)和戴恩 休伯纳(Dwayne Huebner)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后,任职于威斯康辛大学至今。现为该校课程与教学系兼教育政策研究系约翰 巴斯科姆荣誉教授。1989-1990年间,任美国教育研究会(AERA)副主席;1998年,荣获美国教育研究会终身成就奖;2001年,当选劳特利奇20世纪全球最有影响力的50位教育思想家之一。其著《意识形态与课程》和《官方知识》被国际社会学联合会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教育著作,《教育的“正确”之路》被美国两个“教育研究会”(AERA和AESA)分别授予“杰出评论家奖”和“卓越图书奖”。作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创立者和最早在北美倡导批判教育运动的领军人物,阿普尔被巴西批判教育家誉为“世界上致力于批判和民主教育的最为杰出的学者之一”。
致谢
中文版序言
Foreword to the Chinese Edition of Can Education Change Society?
第1章 教育能够改变社会吗?
1 1 初想
1 2 回归
1 3 改变学校,改变市场
1 4 情况可以有所不同
1 5 单枪匹马与构筑联盟
1 6 情感上的平等
1 7 深化对问题的思考
1 8 学校何为?
1 9 承担风险
第2章 保罗?弗莱雷与批判教育学者活动家的任务
2 1 弗莱雷、对话与实践
2 2 阶级转换的政治
2 3 教育与权力
2 4 全球化、后殖民主义与教育
2 5 来自底层的知识
2 6 联系历史
2 7 弗莱雷与批判教育:个人花絮
2 8 批判学者活动家的任务
第3章 乔治?康茨与激进变革的政治学
3 1 学校敢吗
3 2 批判教育与灌输
3 3 今日对康茨的思考
3 4 反霸权的教育
3 5 平民教育的要素
3 6 触及儿童
3 7 用官方知识吗?
第4章 杜?波依斯、伍德森与变革的政治学
4 1 从谁的视角来看?
4 2 杜?波依斯与文化和教育的变革
4 3 卡特?伍德森与教育斗争
4 4 黑人教师的生活
4 5 女性教师活动家的角色
4 6 铭记更多人的声音
第5章 保持变革的活力:向“南方”学习
5 1 导言
5 2 阿雷格里港与“全民管理”
5 3 创建“公民学校”
5 4 新学校的配置
5 5 转变“官方”知识
5 6 学校委员会
5 7 评判成功
5 8 潜在的问题
5 9 未来会怎样?
5 10 阿雷格里港的经验
第6章 沃尔玛化的美国:社会变革与教育行动
6 1 谁的社会工程?谁的教育?
6 2 教育、商业与常识的重建
6 3 保守主义改革的国际化
第7章 批判教育、讲实话与反击
7 1 从个人角度出发
7 2 危险行为
7 3 面对权力的威慑,说出真相
7 4 改变权力关系
7 5 回归与反击
第8章 回答问题:教育与社会变革
8 1 构筑运动
8 2 正值形成中的运动
8 3 学校作为创造性地开展批判工作的场所
8 4 谁是教师?
8 5 有可能成功吗?
参考文献
人名与词汇索引
译后记
第1章 教育能够改变社会吗?
1.1 初想
在许多讨论公共议题的书中,“危机”已经成了一个被人们滥用的词汇。然而,对于危机问题的本质,这些书籍,似乎还没有真正揭示。困扰我们的这样一些事情,诸如失业,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房揭抵押品赎回权的丧失,那些被用于救济贫穷、饥荒和流浪人员的项目资金的削减,养老金和医保的没有着落,种族主义的卷土重来,公众的反移民情绪,以及暴力事件,所有这些社会危机,都正在变得日趋尖锐。在学校里面,学生学业成就的差距、学生从学校沦落到监狱(the school?to?prison pipeline)、右派对严肃批判多元主义文化内容的攻击、政府对学校建设经费的裁减、有关政策和媒体机构对教师群体的极端无礼……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所有这一切,也都是人们遭受痛苦的明证。对于我们这些极力想让教育变得名副其实的人们而言,这些危机触手可及。与此同时,这些危机也迫使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教育是否真的能够对此种形势发起挑战,并协助建设一个能够更少反映我们的自私和更多反映我们彼此爱护与个人能够得到解放的社会呢?您将阅读的这本书,就试图认真回答这一问题。
《教育能够改变社会吗?》这本书,与我之前所写的书不同。对于这本书而言,我并不想把它写成一本大部头的理论之书。毕竟,在我之前所写的一系列的书和文章(参见:Apple 1982; Apple 1986; Apple 1996; Apple 2002; Apple 2004; Apple 2010; Apple 2012)中,已经花了大量时间,去分析有关教育是否有独立的权力,抑或完全受制于主流经济和文化关系的问题。虽然我之前的作品,通过揭示右派将教育作为他们彻底重建其社会特权运动的一部分(Apple 2006),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不过,仍然有一些严肃的理论工作,要由这本书(尤其是导论性的第1章和第2章)2来完成。(请保持耐心。这项工作是我稍后几章讨论批判人士和批判工作的重要基础。)但是,其目的既不是为了提出和证明一个新的总体参数,也不是为了给我们回答教育能否改变社会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终极答案。事实上,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清楚地意识到,并不存在终极的答案——除非我们乐于接受这样一种形式的答复:“这个不一定。因为它取决于许多人是否愿意为此付出大量艰苦而不懈的努力。”这样的回答,或许会让你我感到有些沮丧。但它却是实话。
恰恰相反,这是一本注重批判反思和举证实例的书。前面几章,主要回顾了历史上一些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最著名人物的著作。通过聚焦一些来自宰制集团和少数人群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力图说明,他们所做的工作与他们作为批判教育家所提出的问题与职责,是如何关联到一起的。接下来的几章,我给出了两个通过教育实现广泛社会变革的成功案例。其中一个例子,在目标和过程上都具有极端的进步性。但是,对于那些回答教育能否改变社会——或者,至少能够在推动社会朝着某个特定方向迈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问题的人们而言,它都意味着这样一种提醒: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两个案例所展现的那些推动社会变革的原则与实践,可能都无法得到本书许多读者的赞赏。
第一个例子,来自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它详细介绍了那里的人们为进一步实现社会民主化所做的工作。由此,那里的社会职能部门也不得不学会如何不断地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第二个例子,将我们带回美国。在那里,一个巨大的跨国公司(沃尔玛)是如何与极具保守性的经济、文化、宗教及政治团体保持协调一致的。它最终表明,教育有效地发挥着将那种非常另类和非常狭隘的民主观念加以推行并将其合法化的作用。然而,这与成功实现批判式民主的阿雷格里港的意识形态主张,则是背道而驰的。
尽管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反思,既包括美国国内的学者,也包括美国之外的学者(保罗?弗莱雷,属于后者;乔治?康茨、杜?波依斯和卡特?伍德森,属于前者),与此相应,我所举证的例子也分别取自巴西和美国,但是,我并不认为它适用于所有的民族和任何的时代。因此,读者需要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看看我这里的反思、案例和论述,是否符合你的实际情况和你所在的社会情形。背景是重要的,尤其是当我们对教育进行批判性的反思的时候,它就会显得更加重要。
因此,对于许多其他领域的学者而言,这是一本更具个人性质的书。这种个人性,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它基于我试图找到这样一个棘手问题的答案的想法,或者说,它也源于我因无法简要回答教育能否改变社会这个问题而产生的那种挫败感。3其次,其个人性也体现在,我所发现的一些具体实例,它们能够对这一问题做出有效的回答。再次,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我个人在诸多概念和政治地带的一次旅行——在这里,我想寻求一种为人们所不懈追求的那种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公正价值,与此同时,我也想寻求一种更能响应民众诉求和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的社会。这次旅程,就从当前这个导论性的章节开始。最后,其个人性也体现在,后面一章我将讲述的由于参与公共行动而给我带来的“麻烦”,但是,这种事情最终改变了我、我所在的机构以及和我共事的人们。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开始这次旅程吧。
1.2 回归
在我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刚刚从阿根廷回到威斯康辛。在那里,我与社会变革的支持者们和教师工会的活动家们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为他们做了多场演讲。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里,大家就像置身另外一个世界。教职人员联合会(SUTEBA)和其他教育工会,与更为庞大的劳动权益保护机构有着清晰的从属关系。他们刚刚从国家政府那里,受到一份实至名归的嘉奖。在那里,各级各类的教师和其他教育者,不仅对他们自身应当享有的权利有很高的热情,而且对于自身所应担负的责任也十分清楚。教师以及整个工会,在教育政策中都有强大的话语权。失业者会被组织起来,并让他们参与到能够使他们获得应有尊重的社会和教育事业当中来。在那里,教育、财政和意识形态对他们的支持,被看作是持续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的进步议程的核心部分,而且他们用于教育的GDP份额,也远高于那些通常被视为“更为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
我无意粉饰阿根廷的政治和教育形势,因为在那里,不仅存在着手段与目的以及时常以右派和左派来划分的各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重要矛盾,也存在着社会各个领域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出现过两种“新自由主义”,即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的“New Liberalism”和20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以来的“Neo?liberalism”。对于二者之间的差别,中国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译者认为,导致这种忽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在西方(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中,并没有出现过罗斯福新政时期的“New Liberalism”,或者说罗斯福新政时期的“New Liberalism”并没有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中得到广泛传播。其二是,在英语中,“new”和“neo”来自同一词根(希腊语中的“neos”),它们之间并没有意义上的区分(都表示“新”的意思),而理论界有关“新”与“旧”的说法往往也只是一个时间维度上的区分,因此,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也就有了两种“新自由主义”。不过,对于这个为西方(欧洲)世界广泛使用的“neoliberalism”而言,它同时也是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描述这一“私有化”和“市场化”新趋势的共有词汇,而“new liberalism”的语境似乎早已淡出了这个时代。然而,在阿普尔的思想中,其“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的社会理想是与罗斯福新政时期所提出的“new liberalism”密不可分。故而,我们十分有必要将这两种新自由主义分别命名。按国内有关学者的解读,前者应该译为“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参见:李小科.澄清被混用的新自由主义——兼谈对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翻译[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因此,为区别和强调起见,在本书中笔者将“neo?liberal”或“neo?Liberalism”统一译为“新古典自由主义”。——译者注和新保守主义势力对学校、课程、教师、工会和现行政府政策的攻击。但是,清楚的一点是,尽管那里现行政策进步的速度往往还有些迟缓,但是,从整体上看,它们毕竟还是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和“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两项政策,似乎并不能说明那里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它才能给人一种振奋人心和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威斯康辛和美国其他地方,协调一致、精于策划和资金充足的右派多数群体,已经成功打击了教师、公职人员(public employees)、工会、学校、课程,并同时削弱了少数群体的选举权以及政府对备受争议的集体权利所担负的责任。相比之下,阿根廷的主流话语和主流政策则一再提醒我们,在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我们自己已经朝着右派的方向走了多远:4人们集体协商的权利已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教育只被看作是一种生产考试分数和温顺员工的工厂;教师和一切公职人员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合理的医保和养老资金面临威胁;妇女丧失了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环境保护的议程正被取消;经济不平等是他们几十年政策所收获的最高回报,而且现在仍在继续加剧。此外,对有色人种监禁率的统计,是一个国家的耻辱。所有这一切,都与那些见利忘义的立法相伴而至。这些立法,不仅试图压制穷人、老人、有色人种的选举权,也试图压制一切可能对右派所认为的“坏”政策——因为这些政策所表达的是,对那些在社会上掉队的实有人群的同情与尊重——表示赞成的人们的选举权。然而,这样的立法,显然已经脱离了其伦理的轨道。
在我们国家,如果那些饱受资助且能充分享有公共教育的人们,和那些在这些机构当中工作的人们,都被妖魔化了,我们该怎么办?为什么每当我们面临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候,都非要把学校教育推出来承担责任?为什么每当金融部门在和经济大亨们的角力中濒临溃败时,都要拿学校和公职人员说事?为什么这些人都热衷于通过掠夺工人的劳动成果来“力争上游”,却不花心思琢磨为什么有那么多工人丧失了他们本应享有的养老和社保待遇?当然,这些都是非常难以解答的问题,其中一些,也是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试图予以回答的问题(Apple 2006)。但是,日益清楚的一点是,学校正在遭受一种有悖其本质的待遇——它被看作是引发这些问题的关键因素。为此,(通过私有化、竞争和加强中央控制这一系列举措的奇怪组合)彻底改变学校,就显得势在必行。“好的”学校,只是那些严格遵照公司议程和公司形象办学的单位。而其余的学校,则都是“坏的”。而且,学校也需要一种竞争机制,来加强对其教职员工的控制。然而,由此以来,不仅人们普遍丧失了其集体责任感,就连作为一种集体过程的学校教育本身,似乎也成了市场法则和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敌人,或是被看作破坏二者之纯洁性的根源。
装 帧:平装
页 数:241
版 次:1
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