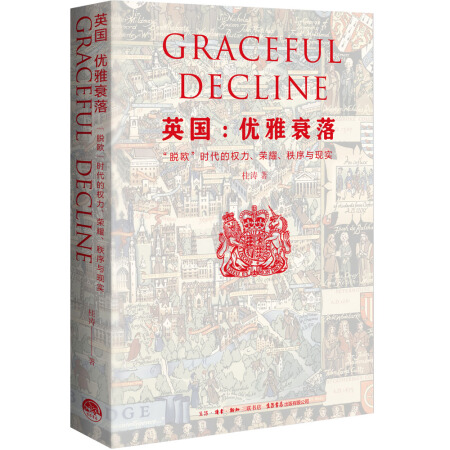
标 签:
“脱欧”公投像一把无情的手术刀,将英国的表皮瞬间切开,把深藏其下、Z真实的繁复肌理与血脉呈现出来。“脱欧”所带来的刺激与冲击恰恰引起英国Z自然的应激反应,这反应是欣喜、愤怒、后悔、无奈,它们就是Z真实的“优雅衰落中的英国”。
新华社驻伦敦记者桂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与采访、感受,试图在“脱欧”这个节点去理解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解读“脱欧”背景下的英国,从中串联起英国的历史与文化、民族与宗教、学术与政治……这里既有大英帝国荣耀的过去,比如多佛和朴茨茅斯;也有萧瑟的现在,比如“西方瓷都”斯托克城。他向“唐顿庄园”的女主人了解英国贵族的生活现状,也采访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校长,去探究自由与秩序的交点。英国的衰落是无人否认的,但这个衰落的过程持续了一百年,这份优雅从容,也能让我们看见社会与人性。
桂涛,新华社记者,2007年参加工作,现为伦敦分社时政记者,负责英国内政、外交中英文报道。2017年获“新华社十佳记者”称号。曾常驻非洲,著有《是非洲》一书。桂涛以自己在英国多年的工作与生活经历切入,试图在“脱欧”背景下去理解英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学术政治,从“优雅衰落”中看“崛起的启示”。作者曾赴二十余个英国主要城镇走访,也与英国前副首相、五大高校校长、军情五处前负责人、数十名两院议员等人当面交流,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序:优雅衰落/004
希斯罗:与英国立约/011
多佛:谁是英国人?/029
唐宁街10号:府院之争/049
威斯敏斯特宫:权力运行/085
舰队街:新闻界兴衰录/0109
斯托克:瓷都兴衰录/131
斯特拉福德:莎士比亚会选择“脱欧”吗?/149
波士顿:“脱欧”小镇/169
海克利尔:贵族今安在?/189
贝尔法斯特、德里:墙与界的诅咒/208
邓迪:独立之城/230
牛津:38所大学/248
剑桥:大学无围墙/267
海伊:觐见“书心王”/287
普利茅斯、朴茨茅斯:海洋之国/307
英吉利海峡:假如没有这道海峡
这镶嵌在银灰色大海里的宝石,那大海就像一堵围墙,或是一道沿屋的壕沟,杜绝了宵小的觊觎,这一个幸福的国土,这一个英格兰。
——莎士比亚《查理二世》
海峡
每个国家都是地理的囚徒,它如何发展、机遇何在、成就如何最终都与它的自然地理特征相关。各国的地缘政治学家总在试图用数据、逻辑推理与想象力向我们证明:这种关联性往往比我们想象得要紧密得多。我不知道有没有一门叫作“假设地理学”的学科,专门研究以下这些“没有意义”的问题:“假如喜马拉雅山脉的平均高度是现在的一半,将对印度洋上吹来的湿润气流有何影响?这将让南亚、中亚和东亚与今天有何不同?”“假如地中海被古希腊人用人工填海的方式填平,欧洲与非洲形成新的‘欧非洲’,工业革命还会率先在欧洲发生吗?非洲还会像现在这样是世界上最穷困的大陆吗?”
我没有电脑软件和数学模型,我只能用常识和想象力推测:如果没有英吉利海峡、不列颠群岛在地理上与欧洲大陆相连,那么英国将完全不是今天的模样,英国将不再是英国。
如果没有英吉利海峡,中纬度西风和北大西洋暖流仍将主导英国的气候,但出名的岛国雾气可能会变少,伦敦将不再是“雾都”,英国的天气也不会再那么善变,英国人可能不再是爱聊天气的民族。
如果没有英吉利海峡,英国可能和法国这样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因为陆地边界防御的需要,发展出强大的陆军、借助军队统治的强大国王,以及满足随时调集军队、抵御入侵的专制制度,这样它就很难产生始终与国王实力相当的贵族,无法在王权与议会漫长的博弈与妥协过程中产生出确认“王在法下”的1215年《大宪章》和确立宪政制度的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可能不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个人自由无法得到促进,古老君主制与现代民主制度也无法像今天这样紧密结合。
如果没有英吉利海峡,可能也不会有主导国际事务长达一个世纪的大英帝国。正是因为英国和欧洲大陆隔离,因此它既关注欧洲事务,同时也面向海洋发展。在自由贸易、舰队和枪炮的帮助下,英国最终从岛国发展为以贸易立国、靠海外掠夺强盛的帝国。
如果没有英吉利海峡,英国将失去对欧洲大陆的天然屏障,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军队可能早已征服不列颠,世界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如果没有英吉利海峡,英国人可以更方便、更频繁地开车去法国度假,在汽车后备厢里装几瓶便宜的波尔多红酒带回家,英格兰东南部在过去几十年里疯长的房价也可能因为大面积建筑用地的产生而得以平抑。
如果没有英吉利海峡,失去了“岛国情结”的英国人还能否写出《鲁滨孙漂流记》《金银岛》《乌托邦》和《新大西岛》这样的“海岛文学”,不得而知。
全是因为那条海峡,英国才成了今天的英国。
斯特拉福德:莎士比亚会选择“脱欧”吗?
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笨拙的伶人,登场片刻,便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去,这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却一无所指。
——莎士比亚《麦克白》
……
斯特拉福德镇上都铎王朝时期造型的房屋已被改造成售卖鹅毛笔、十四行诗诗册的纪念品店和提供中世纪饮食体验的酒馆,接待每年来自全球的50万游客。但游客来了又走,这个人口约三万的小镇总体上仍保持着对世事的超然。大部分人的生活还是围绕教堂、酒吧、《斯特拉福德灯塔先驱报》以及各种俱乐部、慈善商店。这些年来唯一能让镇上居民“不淡定”的事是邻近的伯明翰将自己的机场命名为“莎士比亚机场”。但斯特拉福德人最多也只会义愤填膺地说一句:“他们可真会开玩笑!”
莎士比亚一生共写了154首十四行诗、37部剧本,48岁后封笔,从伦敦回到斯特拉福德,并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四年。如果他活到今天,一定还能在小镇上轻松找到自己在亨利街的住所。他走出家门,左转并沿着亨利街前行,不久就会经过一所当年属于铁匠理查德?霍恩比的屋子,那屋子如今已是莎士比亚诞生地的礼品商店,童年的莎士比亚也许就在这屋前等待霍恩比的孩子一同出门玩耍。在快要走到那条以大桥命名的街道终点时,他会随着弯曲的街道进入中世纪的克洛伯顿石桥,这座埃文河上的桥如今仍然是从南部进入斯特拉福德的入口。大桥街28号是当年他父亲的朋友亨利?菲尔德的家,菲尔德的儿子理查德曾于1593年在伦敦出版了莎士比亚的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从斯特拉福德高街上的巴克莱银行拐弯,他会经过一家门牌号为高街1号的礼品商店,上面挂着“贸易点”的招牌。当年这里是一座小监狱,
门口常常放着一个拘禁犯人的笼子,后来它成为莎士比亚的小女儿朱迪斯与烟草商人托马斯?奎尼的家。
莎士比亚的亲家、布匹商人理查德?奎尼就住在同一条街上的31号。奎尼在1598年10月25日写给莎士比亚的一封信被保存在斯特拉福德的档案馆里。这片七厘米长、五厘米宽、满是霉点的纸页偶然发现于两百年前,如今被神圣地命名为“奎尼之信”。
信中,奎尼向“亲爱的好朋友、同乡威廉?莎士比亚先生”借30英镑(约合今天的3750英镑),但后来的研究证明,莎士比亚并未收到此信。奎尼的邻居、高街32号当年住的是亚麻织品零售商丹尼尔?贝克,是个严厉的清教徒,也是斯特拉福德镇上少有的几个思想狭隘、官气十足的人之一,被莎士比亚的大女婿约翰?霍尔称为“坏蛋”。贝克在担任镇长时曾禁止艺人表演,不知道他要是看到今天镇上立着的铜像是莎士比亚《皆大欢喜》里的小丑会作何感想?就在这同一条街上,还有一座用黑木条装饰的三层小白楼,外墙上刻着字母“TR”,那是这房子曾经的拥有者托马斯?罗杰斯姓名的首字母缩写。这个精于算计的肉贩子当年做出的最明智决定可能是将女儿嫁给另一个来自伦敦的肉贩子罗伯特?哈佛,托马斯因此得到了一个名叫约翰?哈佛的外孙,正是他后来移民美国,命名了哈佛大学。托马斯当年的肉铺、他的故居现在被游客称为“哈佛屋”。
当莎士比亚走到高街尽头,他会走上礼拜堂街。那里曾住着朱拉埃?肖(正是这位好友曾见证他在遗嘱上签下自己姓名),莎士比亚唯一的外孙女伊丽莎白?霍尔和她的丈夫也曾在这条街上居住。街尽头靠近行会礼拜堂的地方是莎士比亚的另一处故居,如今以“新居”命名。这几间精巧的砖木房子是当时镇上第二大的宅子,莎士比亚在成为伦敦知名演员与剧作家后花了用五年存下的120英镑买给自己养老。莎士比亚可能会对“新居”现在的样子颇为吃惊,那里是一座根据维多利亚时代园艺书中所载的样式设计的小花园,里面摆放着一些与他相关的现代艺术品,买了景点通票又时间充裕的游客才会到此一游。就在莎士比亚和妻子安妮迁入“新居”的前一年,他们11岁的儿子哈姆奈特夭折,据说莎士比亚当时正在写作《约翰王》,其中恰好记录了一个母亲失去年轻儿子的悲痛:“悲哀代替了不在我眼前的我的孩子的地位;它躺在他的床上,陪着我到东到西,装扮出他的美妙的神情,复述他的言语,提醒我他一切可爱的美点,使我看见他的遗蜕的衣服,就像看见他的形体一样。”
再往前走,莎士比亚会经过爱德华六世文法学校里看起来有点歪的二层长楼,他也许会记起自己儿时在那里死记硬背拉丁文时的场景,或是校长西蒙?亨特向学生们讲授奥维德诗歌时的愉悦。那时这个学校还被称为“国王新校”,离他父亲和其他市政官一起出席会议的市政厅很近。如果他停下脚步透过学校含铅的玻璃窗向里面张望,他会看到伊丽莎白?杰尔德厅,他曾在那里观看行吟艺人的表演,英国知名的“莱斯特勋爵戏班”也正是在那时来到斯特拉福德演出,这里就是小莎士比亚剧院艺术的启蒙地。
在斯特拉福德,莎士比亚走完自己从出生到死亡的旅程只要十几分钟。路过几户在窗台上放着工艺烛台和瑞典达拉木马的人家,莎士比亚就能最终走到自己在圣三一教堂的安息地。教堂在埃文河畔,尖顶的哥特式建筑与散落的、几乎已被磨平的墓碑被青苔与藤蔓包裹,像是一个巨大的时间机器,将来访者一下子带回几百年前。四百年前,莎士比亚的遗体被安葬在回荡圣歌、闪烁烛光的教堂内,如今要看他嵌在地下的墓碑先要往入口处的木盒里捐几个硬币。墓碑上是莎士比亚自撰的墓志铭,要看清它,只能俯身屈膝,甚至单脚下跪,参观者倒也不介意,反正他们是来“朝圣”的。
那铭文写道:“蒙天主仁慈,朋友们请不要碰触我的墓。那些让我的墓地保持原样的人会被保佑,而碰到我身体的人将遭到诅咒。”据说正是这句咒语打消了英国人将莎士比亚的遗骸移去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想法,不少崇拜者们认为,莎士比亚本该在那里和拜伦、弥尔顿、哈代一同长眠。两百年前,几个工人挖地窖时意外导致莎士比亚墓地的泥土塌陷,形成一个可直通坟墓、状如拱顶的空洞,但没有人敢去打扰这具由一段诅咒护卫的遗体。
据说一个老司事曾斗胆在洞口向里瞥了一眼,但既不见棺椁,也不见骸骨,除一抔黄土外什么也没有。
贝尔法斯特、德里:墙与界的诅咒
墙
今天的北爱被一堵墙和一条边界“诅咒”。
墙是首府贝尔法斯特的和平墙,它以“和平”为名,却是因恨而建。那条边界是北爱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五百公里长的曲折边界线,“脱欧”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让它可能重新点燃北爱的仇恨。
我从小就对守护家乡的城墙有特殊的感情,一直对“高筑墙”带来的安全感深信不疑。后来我到了甘肃,看到丝绸之路上风化到只剩土墩的明城墙,还有墙边兰新线上呼啸而过的高铁,开始思考筑墙与通路这两种古老中国与外界相处的方式。再后来,我收藏了一小块柏林墙的碎片,上面油漆喷涂的标语已经难以辨认。我开始怀疑,墙是否都会倒掉?
是筑高墙还是通大路?这是每个时代和民族都绕不过去的问题。今天的英国也在作答。
贝尔法斯特的和平墙其实并非一堵墙,而是在这座城市各处居民区里的一段段隔离设施,有的是砖筑,有的是隔离板加铁丝网,三四米高,最长的有几公里。北爱人赋予隔离墙“和平”之名,是因为这里混居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总是争斗不止,竖起高墙,能挡住不少双方互掷的石块、酒瓶或是汽油弹。
北爱的友人告诫我注意安全,说和平墙附近不太安全,最近还有游客大巴车被飞来的石块击中,据说还有人被墙两边“准军事组织”的冷枪所伤。朋友建议我像其他游客一样,坐出租车从墙边慢慢驶过,最多停下来拍张照。但我还是选择步行参观。
哪有那么恐怖?那和平墙的墙头上明明还有鸽子在漫步。墙两边的居民区静悄悄的,站在墙这一侧,听得见对面的车响。不少墙面上成片喷涂着各派的政治涂鸦画,上面有各种政治符号,最常见的是爱尔兰共和国的三色旗、红手掌、匕首、AK47步枪、火箭筒、牢房、铁丝网等,鲜亮的红色、绿色、黑色、黄色仿佛混杂着各种情绪,让这墙转述几十年来的喷绘者想说的话:有呼吁释放政治犯的,有要求爱尔兰统一的,有强调北爱是英国领土的,有纪念各次冲突中死亡的圣徒与烈士的,还有声援巴勒斯坦和加泰罗尼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有的墙段上,画着白色的十字架,意味着那里曾经有人在教派冲突中死去。
在一段墙面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写下自己的心里话。我看到一个美国游客留下涂鸦:“哈哈哈!我们的墙将比你们的还大还高!”他指的是特朗普总统下令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修建的隔离墙。
沿着和平墙行走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行。一边是记录在墙上的苦难与仇恨,另一边是杂货店、酒吧、公交车站和闲聊的人。
这墙断断续续,我常常走着走着,就从挂着爱尔兰共和国国旗、窗户里摆放圣母像、要求结束英国在北爱统治的天主教徒居住区,走到了挂着英国米字旗的新教徒居住区,不知不觉。几所学校就
建在高墙下,教室窗外就是高墙。墙边住宅栅栏里,还立着上个圣诞节后没来得及清理的圣诞树。这让我想到,墙两边的人过的是同一个圣诞节。
剑桥:大学无围墙
我发现剑桥大学在任何意义上而言都是一个庇护所。
——剑桥大学拉丁文教授、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豪斯曼
牛剑
在不列颠民族的精神地图上,英格兰中部的牛津与剑桥格外闪亮。两所大学都源自中世纪的宗教世界,它们是矗立在城市中的一座巨大坟墓,多少观念与思想经过历史长河的筛检后,埋葬其中。
剑桥确实和牛津太像了,我常常走着走着就弄错了所在。它们都有一座以圣母名字命名的主座教堂,一个以鬼怪故事闻名的钟塔,一座浪漫的叹息桥,一条由站在船尾、手持竹竿的撑船人主宰的河流,几十座传承不同世界观与成功观的学院,一段段真假难辨的传说。这些传说为两座大学蒙上一层神圣的光。比如剑桥大学那个关于王后学院里木头搭成的“数学桥”的传说。据说该桥为牛顿所建,整座桥原本没有使用一个螺丝,但后来一个好奇的学生把桥拆掉研究,却无法按原样装回去,只能用螺丝钉重修此桥。这个动人的故事其实是后人杜撰,因为“数学桥”建成时,牛顿已经去世22年。
两座城市都是宽容的。你总能遇到踩着高跟鞋、穿着渔网袜的异装癖者,骄傲地走在街头,完全不顾路人的眼光。如果正好赶上周末,打扮成漫画形象去参加各种主题派对的年轻人会涌上街头,你也经常能看到蝙蝠侠牵着玛丽兄弟的手,或是穿着哥特式服装的女孩搂着绝地武士。
但只要仔细观察,这对如此相似的姐妹学校又是如此不同。德国记者彼得?扎格尔在他的《剑桥:历史和文化》一书中写道:“哲学博士的头衔在牛津叫作D.Phil.,在剑桥叫作Ph.D.,这是微不足道的学院小事吗?才不是呢。这是人们一直精心维护的最基本差别。”牛剑之间的其他差别包括:虽然两校都有“莫德林学院”和“王后学院”,但它们的英文拼写方式与来源均不同;牛津的学生称老师为“导师”(Tutor),剑桥的学生则称他们为“辅导老师”(Supervisor);牛津各个学院的内院叫作“方庭”(Quad),剑桥则叫“大院”(Court);牛津每个学院有“联谊室”(Common room),剑桥则叫“混合室”(Combination room)。
“牛津与剑桥究竟有何差别?”我曾将这个问题抛给两校的校长。他们在对对方学校的一番夸赞后,给出了如下的回答:牛津大学校长理查德森说:“历来剑桥大学常被视为科学类院校,牛津大学则被视为人文类院校。而且牛津大学更关注公共生活,比如说我们培养出了27位首相,剑桥大学的这个数字可能是我们的几分之一。与剑桥相比,我们有更多的学生选择投入公众事业。”
剑桥大学校长斯蒂芬?图普说:“历史上,人类知识中最为根本的发现都出自剑桥,牛津有一些,哈佛和斯坦福也有一些,但出于某种原因,这些最为重要的发现极大比例都出自剑桥。我想这是源自这里对于提问的开放精神,以及对于宏大图景和思想的探索精神。我并不是说这些在我们的姐妹学校中不存在,但似乎在剑桥的存在感极强。”
当我在餐桌上把两位校长的回答告诉77岁的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时,这个秃顶的小老头儿没有抬头,他用手中的刀叉切着盘里的奶酪块,不屑地说:“他们没说对。”
麦克法兰的办公室在剑桥最出名的国王学院,窗外是学院入口处19世纪的哥特式门楼,和大草坪中间孤单站立的学院创办人亨利六世的铜像。在这座学院里,麦克法兰的办公室被称为“G2”,那是它在学院独特的房屋编号体系中的名字,它是大楼“G”入口的第一间。办公室大门门头上是细长的白木牌,上面用黑油漆写着“麦克法兰教授”和另一个教授及一个博士的名字,屋子是他们三人共用。想必是办公室的主人来了又走,木牌刷了一层层白漆,微微隆起。麦克法兰著作等身,他是英国科学院与欧洲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是世界现代性的本质。教授陷坐在布沙发里,周围是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用过的柜子、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用过的无线电广播。我想当教授去世后,他的名字会和“G2”永远联系在一起,就像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开山鼻祖罗杰?弗莱在国王学院是“J10”,凯恩斯是“P3”,“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是“X17”。
麦克法兰在牛津读完本科和博士,在那座城市住了12年,又在剑桥住了45年,他始终在对两座学校做“田野调查”。在他眼中,“牛剑”有三处不同:剑桥更美,“在英国玩,如果有一周时间可以去牛津,如果只有一天,要来剑桥”;剑桥的教授退休后在各个学院仍保留自己的办公室;剑桥诞生的天才更多。
“比如约翰?哈林顿,他就是个被我们忽视的天才。”麦克法兰对我说。曾在国王学院读书的哈林顿是个诗人,但他载入史册的原因却是因为他的发明——冲水马桶。哈林顿曾向自己的教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介绍自己的发明,女王还曾亲自试用。麦克法兰和他的团队目前正在和一个世界知名的马桶厂商联系,希望让他们为国王学院设立一笔基金,增加这个古老学院里厕所的数量。这并非麦克法兰第一次利用国王学院的历史来谋划它的未来。他目前担任学院草地上一块石碑的“看护人”,那块白色的大理石碑上刻着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名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曾在国王学院读书的徐志摩成了中国游客到访这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麦克法兰和他的团队还在积极推动举办“徐志摩诗歌艺术节”和开设“国王学院徐志摩纪念花园”。
“石碑的看护人要做什么?”我问麦克法兰。
“过去看一看,擦一擦吧。”他说,“我猜他们让我当‘看护人’主要是守住这块碑,别让牛津拿走了。”
海伊:觐见“书心王”
旧书店是人类所有异端思想避难的祭坛,我们最狂野、最黑暗、最自我分裂的想法都如绝望的匪徒般藏身于此。一间旧书店就是一个炸药库,一家毒药店,一间鸦片馆,一座女妖岛。
——英国哲学家约翰?波伊斯《论文学之乐》
海伊
我登上开往威尔士的火车去觐见“国王”。车上,我翻开布斯的自传《我的书城》,读起他和他的书城往事。
55年前,布斯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爱书的他花700英镑买下镇上的老消防局,开了一家旧书店。此后,布斯不断从世界各地用集装箱将人们丢弃、贱卖的旧书运回海伊出售,来小镇淘书和开书店的人也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在海伊的鼎盛时期,布斯曾在这里开设七家书店,坐拥书城。
在布斯的带动下,这个只有1500人的小镇现在拥有近三十家旧书店,密度比伦敦的超市高得多。小镇上还有不少古玩店、手工制品店,旧书、古玩琳琅满目,吸引各地的游客。海伊早已是全球爱书人、藏书人和淘书人的“精神麦加”。
布斯是海伊人的“国王”。这不仅因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书镇”概念、并将其在海伊发扬光大的人,也因为他曾买下镇上那座建于11世纪、如今已残破却仍在小山上俯视书镇的城堡,并在1977年愚人节宣布海伊为独立王国。布斯和全世界开了个极其认真的玩笑。
《我的书城》出版于1999年,布斯在他的签名上还特意画上一个王冠。
国王今安在?
海伊不通火车,需坐火车到最近的赫里福德市,再转乘近一个小时的大巴车才能到。看着路边的农田与牛群,闻着不断飘来的牛粪味,我惊叹这与世隔绝的山地竟然诞出了传奇的书镇。如果不是因为旧书,海伊可能根本是个连绝大多数英国人都不知道的地名。历史上,海伊是个贸易集镇,商贾众多。传说罗马帝国瓦解后,率领圆桌骑士团统一不列颠群岛的亚瑟王就曾在小镇附近战斗,留下一处遗迹。除此之外,海伊默默无名。
20世纪60年代,海伊和许多威尔士小镇一样,随着采矿业的衰落而颓败。就在布斯大学毕业后回到海伊的1962年,运营了近百年、连接小镇与外部世界的唯一一座火车站也因英国铁路系统整合而被关闭至今。
我跟着那些背着独立书店印制的布口袋、前来朝圣的书虫们一起,从公交车站走进山脚下的海伊。这里确实是个书镇,它符合爱书人对天堂的一切幻想,就像瑞士的拉绍德封之于钟表收藏家、德国的慕尼黑之于啤酒爱好者、英国的利物浦之于披头士乐队的发烧友。大大小小旧书店外一排排的书架,上面贴着“一本50便士、三本1英镑”,咖啡店里用书本和书页装饰,“初版书”“签名本”“Folio版(由伦敦The Folio Society出版社精选出版的精装版)”这样的术语经常能从自来熟的淘书人嘴里听到。这里有电影院改建而成、摆放20万册书籍的旧书店,有专卖诗歌或是儿童图书的旧书店,还有以“谋杀犯与暴力犯罪”为名、专卖惊悚小说的旧书店。在爱书人眼中,海伊镇是个走几步就有惊喜的地方。他们在旧书堆里翻检,用背包载回落满灰尘的宝贝,摆放到家中书架上各种专题收藏目类下,然后对着一脸羡慕的藏友回忆自己的淘宝故事。
但我隐隐感觉,这绝非书镇的全部,我想弄清这桃源小镇存在的内在逻辑,以及电子化阅读的冲击下它的未来。
在我发出采访申请后,布斯的秘书很快回信,说国王可以在家中接受采访。今天,在书镇上的“海伊国王书店”,还能花一英镑买到王国的护照,花三英镑买一份受封骑士勋章的证明。书店店员会向来访者介绍海伊的国王,来访者们也听得兴致盎然。“因为他有城堡,国王都拥有一座城堡。”店员常常对来访者这样解释布斯国王的身份。海伊镇上,一些书店还悬挂布斯国王2009年发布的标准照。照片是英王亨利八世的那张著名画像,只是脸用修图软件换成了布斯的。因为几年前的一次中风,照片上年近八十的布斯歪着嘴,眉宇间的神情,与其说是威严,不如说是孩子般的顽皮。
国王住在海伊镇外一英里的小山上,绿树环绕。我按着他秘书发来的地图一路寻找,沿路都是草场,偶尔有家小旅店,我甚至好几次怀疑走错了方向。爬上一条陡坡,终于来到布斯三层楼的大宅。这里与世隔绝,门前还有松鼠爬过。进门处的玻璃窗上是布斯国王的画像,显示着这房子与众不同。
装 帧:平装
页 数:360
印 次:1
版 次:1
开 本:32开
纸 张:纯质纸
正文语种: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