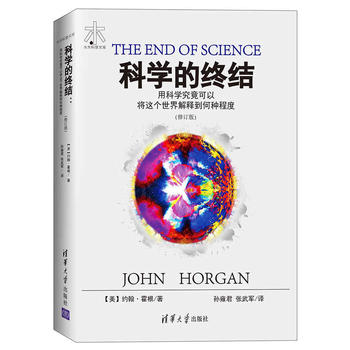
约翰·霍根(John Horgan)是《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其中文版为《环球科学》)的资深撰稿人。他曾两度获美国科学促进会新闻与社会关系促进奖。他著有四本书,包括《科学的终结》(The End of Science,Addison Wesley,1996)和《战争的终结》(The End of War,McSweeney's, 2012)。他的文章登载在《纽约时报书评》《发现》《新科学家》《科学》和《集萃》等杂志上。《科学美国人》是美国历史*长的、一直连续出版的杂志,也是著名的《科学》(Science)的姊妹刊。大众化的高水平学术期刊,有151位诺贝尔奖得主撰稿。自2005年起,霍根就职于史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全美工程类大学排名前五,毕业生就业率和薪资排名前三,被称为“工程师的摇篮”),讲授科学史。
孙雍君,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原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擅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科学方法论思想为指导,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综合考察、分析比较与理论论证等方法。著有《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9月*版)。译著《高级迷信: 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当代科学文化前沿丛书)(【美】格罗斯、莱维特著,孙雍君、张锦志译),《书写生物学: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文本》,科研项目“《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教学内容改革研究”曾获一等奖。
1 第一章 进步的终结
一次关于科学信仰之终结的会议
岗瑟·斯滕特的“黄金时代”
科学是其自身成就的牺牲品吗
一百年前的物理学家到底是怎么想的
凭空杜撰的专利局长
本特利·格拉斯挑战万尼瓦尔·布什的“无尽的前沿”
列奥·卡达诺夫看到了正等待着物理学的艰难岁月
尼古拉斯·里查的一厢情愿
弗兰西斯·培根之“不断超越”的寓意
作为“消极能力”的反讽科学
27 第二章 哲学的终结
怀疑论者到底相信什么
卡尔·波普尔终于回答这个问题:证伪原则是可证伪的吗
托马斯·库恩对自己的“范式”谈虎色变
保罗·费耶阿本德——无政府主义哲学家
科林·麦金宣告哲学的末日已至
“萨伊尔”的寓意
59 第三章物理学的终结
谢尔登·格拉肖的忧虑
爱德华·威滕对超弦和外星人的见解
史蒂文·温伯格空洞的终极理论
汉斯·贝特对“世界末日”的计算
约翰·惠勒与“万有源于比特”
戴维·玻姆——既廓清迷雾又散布神秘烟幕的人
理查德·费曼与哲学家的报复
91 第四章 宇宙学的终结
史蒂芬·霍金的无边想象
戴维·施拉姆——“大爆炸”的大吹鼓手
弥漫于宇宙祭司之间的疑惑
安德烈·林德与混沌的、分形的、永远自复制的暴涨宇宙
弗雷德·霍伊尔——终生的叛逆
宇宙学会变成植物学吗
115 第五章 进化生物学的终结
理查德·道金斯——达尔文的猎犬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的生命观——全是废话
林恩·马古利斯控诉盖亚
斯图亚特·考夫曼精心炮制的有组织的无序
斯坦利·米勒汲汲于永恒的生命起源之谜
147 第六章 社会科学的终结
爱德华·威尔逊对于社会生物学终极理论的恐惧
诺姆·乔姆斯基的玄机与困惑
克利福德·格尔茨永远的烦恼 167 第七章 神经科学的终结
生物学领域的“恶魔”弗朗西斯·克里克杀入意识领域
杰拉尔德·埃德尔曼围绕谜团装腔作势
约翰·埃克尔斯——最后一位二元论者
罗杰·彭罗斯与准量子心智
神秘论者的反攻倒算
丹尼尔·丹尼特是神秘论者吗
马文·明斯基对执着于单一目的深恶痛绝
唯物主义的胜利
203 第八章 混杂学的终结
什么是混杂学
克里斯托弗·兰顿与人工生命之诗
佩尔·贝克的自组织临界性
控制论与突变论
菲利普·安德森论“重要的是差异”
莫雷·盖尔曼否认“别的东西”存在
伊利亚·普里高津与确定性的终结
米切尔·费根鲍姆被桌子驳倒
241 第九章 限度学的终结
在圣菲研究所叩问“科学知识的限度”
在哈德逊河畔会晤格雷高里·蔡汀
弗朗西斯·福山对科学不满
星际旅行的爱好者们
261 第十章 科学神学,或机械科学的终结
J. D·贝尔纳的超凡预见 汉斯·莫拉维克招惹口舌的“特殊智力儿童”
弗里曼·戴森的极度多样性原则
弗兰克·蒂普勒“鬼打墙”的幻觉
欧米加点到底想做什么
277 尾声 上帝的恐惧
一次神秘体验
欧米加点的寓意
查里·哈茨霍恩与索齐尼异端
为什么科学家们会对真理爱恨交加
上帝在啃他的手指甲吗
287 跋 未尽的终结
303 致谢
引言
寻求“终极答案”
科学——纯科学——是否有可能终结?我对这一问题的严肃思考,始于1989年夏天的一次采访。当时我乘飞机到纽约州北部的锡拉丘兹大学去拜访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一位正在那里做访问学者的英国物理学家。在采访彭罗斯之前,我是硬着头皮才啃完了他那部难解的巨著《皇帝的新脑》,但出乎我的意料,时隔数月,经《纽约时报书评》的宣扬,它竟然成了一本畅销书。[1]彭罗斯在书中全面考察了现代科学,发现它存在着严重的缺失。他断言:现代科学尽管有着强大的威力和丰富的内容,但仍不足以解释存在的终极奥秘,即人的意识问题。
彭罗斯推测,理解意识问题的关键可能就隐藏在现代物理学两大理论之间的裂隙中。一个是量子力学,描述的是电磁学以及粒子相互作用的规律;另一个是广义相对论,即爱因斯坦(Einstein,A.)的引力理论。自爱因斯坦以降,许多物理学家都曾试图把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融汇成一个无内在矛盾的“统一”理论,却都以失败而告终。彭罗斯在他的著作中描绘了这种统一理论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它将给人类思想带来怎样的促进作用。他关于奇异量子和引力效应通过大脑扩散的论述是含混而晦涩的,完全没有什么物理学或神经科学的证据,但一旦在某种程度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话,将标志着这是一个不朽的成就,它会一举实现物理学的统一,并解决哲学中*让人困扰的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当时,作为《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专职撰稿人,我认为单凭彭罗斯的这一抱负,就足以使他成为该刊人物专访的合格人选。[2]
抵达锡拉丘兹机场时,彭罗斯正在那里接我。他个头矮小,一头蓬乱的黑发,表现出的神态简直让人无法分清他到底是笨拙还是精明。在驱车返回锡拉丘兹大学校园的路上,他不时地嘀咕着,说不知所走的路线到底对不对,仿佛他正沉浸在某种玄想之中。我很尴尬地发现,尽管自己此前从未来过锡拉丘兹,他却要我来建议是不是要走这个出口,或是不是要在那里转弯,那情景简直就像两个盲人在赶路,居然竟让我俩平安地抵达了彭罗斯工作的楼前。走进他的办公室,就发现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色彩艳丽的喷雾玩具盒,那是一位促狭的同事留给他的,上面赫然标着“超弦”(Super-string)的字样。彭罗斯按下盒顶的按钮,便有一束灰绿色的、细面条似的水雾向房间里疾喷而出。
彭罗斯被同伴这个无伤大雅的小把戏逗乐了。超弦不仅是一种儿童玩具的名称,而且是一种流行的物理学理论假设的、极小的、纯属臆测的弦状粒子的名字。根据超弦理论,这些弦在十维超空间中扭曲,产生了宇宙中一切的物质和能量,甚至产生了空间和时间。许多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都认为,超弦理论可能会被证明为正是他们寻觅已久的统一理论,有人甚至称之为“万物至理”。彭罗斯却不以为然,“不可能,”他告诉我说,“我所期望的答案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对他而言,答案绝不单纯是种物理学理论,一种组织数据和预言事件的方式,他所寻求的是“终极答案”——关于生命的奥秘以及宇宙之谜的答案。
彭罗斯是一位公认的柏拉图主义者,认为科学家不应去发明真理,而要去揭示真理。真正的真理蕴含着美、真实和一种使之具有启示力量的自明品质。他承认自己在《皇帝的新脑》中所提出的见解是十分粗糙的,还够不上“理论”的标准,将来很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尤其在细节上肯定不会完全正确,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比超弦理论更接近真理。我这时插话问道:“如此说来,你是否暗示着科学家们有朝一日将会找到‘终极答案’,并由此给自己的探索画上句号呢?”
彭罗斯不像某些知名的科学家那样,认为回答问题时迟疑不决是丢面子的事,他在回答之前要思索一段时间,甚至在回答的过程中也是如此。“我认为我们不会完事,”他凝视着窗外缓缓说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情不会在某些阶段进展得更快些。”他再度沉思了一会儿,“我想这更意味着答案确实存在,尽管这可能让人觉着很沮丧。”*后一句话使我一愣,于是又问,“那么,对于真理的追求者来说,认识到真理是可达到的,这有什么可沮丧的呢?”“揭示奥秘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彭罗斯答道,“如果所有的奥秘都已被解决,这无论怎样说都是让人十分沮丧的。”说到这里,他微微一乐,仿佛被自己古怪的措词打动了。[3]
离开锡拉丘兹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反复思考彭罗斯的话。科学有可能走到尽头吗?科学家们实际上能够认识一切吗?他们能够驱除宇宙中的一切神秘现象吗?对我来说,想象一个没有科学的世界是十分困难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职业建立在科学事业之上。我之所以成为一名科普作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认为科学——纯科学,指仅仅是为了求知的科学——是*崇高、*有意义的人类事业。我们选择了科学,*终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我并非总是这样倾心于科学的。在大学期间,有一段时间我曾认为文学批评是*为振奋人心的智力活动,但后来,当我在某个晚上喝了大量的咖啡,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啃对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的阐释之后,突然陷入了信念危机。睿智的人们已经就《尤利西斯》的意义争论了几十年,但现代的一段批评文字(也是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段批评文字)却是:所有的文本都是“反讽的(Ironic)”,它们具有多重意义,但没有一种意义是*性的;[4]《奥狄浦斯王》《地狱篇》甚至《圣经》,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只是玩笑”,不能仅仅按字面意义去理解;关于意义的争论永远也不会有结果,因为一种文本*的真实意义就是文本自身。当然,这段妙论也适用于批评家们。人们陷入解释的无限回归之中,没有一种解释代表终极的结论,但每个人都仍在争论不休!目的何在?难道仅仅是为了使每个批评家都变得更机智、更有趣吗?于是,所有这些争论在我眼里顿然失去了意义。
尽管我主修的是英语,但我每学期都至少要选修一门科学或数学课。致力于微积分或物理学中的问题,标志着从纠缠不清的人文科学的羁縻中超脱出来的可喜一步;我在求得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的过程中发现了巨大的乐趣。我越是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尴尬前景感到灰心,就越是欣赏科学那种简洁而毫不夸饰的方法。科学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批评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力所难及的。理论必须接受实验的检验,与实际相对照,并剔除所发现的缺陷。科学的威力是无法否认的,它给我们带来计算机和喷气式飞机,带来了疫苗和热核炸弹,带来了改变历史进程的技术,不论是福是祸。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知识,如文学批评、哲学、艺术、宗教等而言,科学能够给出关于事物本质的更为可靠的见解,使我们更有奔头。这种内心的顿悟,引导我*终成了一名科普作家,也形成了我对科学的基本看法:科学至少在原则上处理那些能被解答的问题——当然要提供足够的时间和条件。
在与彭罗斯会晤之前,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科学是没有尽头的,或者说是无限的。科学家可能在某一天发现一种威力巨大的真理,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有待研究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在当时的我看来,*多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或是向大众推销科学(或科学书籍)时的夸夸其谈。但彭罗斯在思索终极理论可能性时的那种热切而又矛盾的心理,迫使我重估自己关于科学未来的看法。这一问题时时纠缠着我,使我去思索科学的限度(如果存在的话)究竟是什么。科学是无限的,还是如我们的生命一样终有一死?如果是后者,那么科学的末日是否已经在望?末日是否已降临到我们头上?
以采访彭罗斯为开端,我后来又发现了另外一些同样在探索着知识的限度问题的科学家:一心寻求物质和能量的终极理论的粒子物理学家,试图精确理解宇宙怎样产生以及为什么产生的宇宙学家,意欲确定生命怎样发生以及何种规律支配生命发展的进化生物学家,探索着产生意识的大脑内部活动的神经科学家,还有混沌和复杂性的探索者,他们希望能借助计算机和现代数学方法为科学注入新的活力。我也访问了一些哲学家,其中有的怀疑科学是否能不断获得客观的绝对真理。我在《科学美国人》上撰文介绍了许多这类人物。
在我*初萌生写作本书的愿望时,曾把它设想为一部系列人物传记集,如实地描述自己有幸采访过的那些各具魅力的人物,不论他们是在追求真理还是在逃避真理。至于哪些人物对科学之未来的预测是合理的,哪些人的不合理,我打算把它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毕竟,又有谁真的知道知识的终极限度可能是什么呢?但慢慢地,我开始认为“我知道”,并逐渐相信有一种解释方案比其他的更有说服力。我决定放弃恪守新闻工作客观性原则的初衷,写一本毫不掩饰批判性、论辩性和个人观点的著作,在把焦点仍然聚集在一个个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前提下,书中应更多地体现出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自己提出的方案与自己的一种信念是一致的,即几乎所有关于知识的限度的主张都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烙印。
在今天,人们已普遍认识到科学家不仅仅是求解知识的机器,他们也受到激情和直觉的引导,就像他们要受无情的理性和数学计算的约束一样。我发现,在面对认识的极限时,科学家们更像普通人一样,易受到自己的恐惧和欲望的左右。对于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来说,*位的需要是揭示关于自然的真理(另外,当然也需要荣誉,希望得到承认和地位,渴望能为更多的人谋福利),他们想“知道”,他们希望——同时也坚信——真理是能够达到的,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理想,或是一种可无限逼近但永远无法到达的“渐近线”;他们还像我一样,坚信追求知识是*崇高、*有意义的人类活动。
怀有这一信念的科学家,常常被指责为狂妄自大。事实上也的确有某些科学家狂妄自大,但我发现,更多的科学家与其说狂妄自大,不如说忧心忡忡。真理的追求者们都时光难挨,科学事业正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来自那些对技术深怀恐惧的人们、动物保护主义者、宗教极端主义者以及——也是*重要的——吝啬的政客的威胁。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限制,将使科学事业(尤其是纯科学)在将来的处境更加窘迫。
此外,科学自身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给自己的力量套上枷锁。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把物质运动甚至信息传递的速度限制在光速范围内;量子力学宣告我们关于微观世界的知识总是不确定的;混沌理论进一步证明,即使不存在量子不确定性,许多现象仍然不可能预测;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则消除了我们对实在建构一个完备、一致的数学描述系统的可能性;同时,进化生物学在不断地提醒我们:人是动物,自然选择设计出人来,不是为了让人们去揭示自然的深刻真理,而是让人们繁衍后代。
那些自认能克服所有这些局限的乐观主义者,必然会面临另外的窘境,这可能是所有困境中*恼人的一个:若科学家们成功地掌握了一切可以掌握的知识,那他们再去做什么呢?到那时,人生的目的又将是什么?人类的目的又将是什么?罗杰?彭罗斯自称他对于终极理论的梦想是悲观的,这充分暴露了他对这种两难处境的焦虑。
本书中我所采访的许多科学家,似乎只要涉及上述沉重的话题,无一不被某种深深的不安所左右,但我认为他们的不安有着另外的更为直接的原因。如果你相信科学,就必须接受这种可能性,甚或已具有几分现实性的可能性,即伟大的科学发现时代已经结束了。这里的科学,并不意味着应用科学,而是指那种*纯粹、*崇高的科学,即希望能理解宇宙、理解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这类*基本的人类追求。将来的研究已不会产生多少重大的或革命性的新发现了,而只有渐增的收益递减。
对科学影响的焦虑
在试图理解现代科学家们的一般态度时,我发现来自文学批评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其1973年发表的颇具影响的著作《影响的焦虑》中,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把现代诗人比作是弥尔顿《失乐园》中的撒旦。[5]正如撒旦要通过挑战上帝的完美来维护自己的个性一样,现代诗人也必须致力于一种恋母情结的战斗,以界定他/她自己与莎士比亚、但丁及其他大师的关系。布鲁姆认为这种努力终归是徒劳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位诗人能接近这些前辈们的高度,更不用说超越他们了。现代诗人作为迟来者(latecomers),实际上都是悲剧性的人物。
现代科学家也是迟来者,并且他们的包袱比诗人的更重。科学家们不仅要承受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更要承受牛顿的运动定律、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以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这些理论不仅是美的,而且是真的,被经验所证实了的真,这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无可比拟的。面对布鲁姆所谓的“太丰足所以无所求的传统所带来的种种苦恼、惶恐” [6],许多科学家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奈。他们只能在主导“范式”的束缚下,试着去解答被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傲慢地称作“难题”(Puzzles)的问题,满足于对前辈们那辉煌的、开创性的发现进行精细的加工和应用。他们试图更精确地测量夸克的质量,或去确定一段特定的DNA如何决定胚脑的发育;另一部分科学家正如布鲁姆所嘲笑的那样,变成了“单纯的叛逆者,幼稚的传统道德范畴颠覆家” [7],他们把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理论贬低为脆弱的社会建构产物,而不是在严格检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自然的描述。
布鲁姆所谓的“强者诗人”(Strong poets),承认前辈们登峰造极的成就,但仍然挖空心思地力求超越他们,包括别有用心地误读前辈们的作品,因为只有这样,现代诗人们才能从历史那让人窒息的影响中挣脱出来。也存在着这样的“强者科学家”(Strong Scientists),他们试图误读并超越量子力学或大爆炸理论或达尔文进化论。罗杰?彭罗斯就是一位强者科学家,他和同类的战友们*多也只能有一种选择:以一种思辨的、后实证的(postempirical)方式去追求科学,我称之为反讽的科学(ironic science)。反讽的科学与文学批评的相似之处在于:它所提供的思想、观点,至多是有意义的,能够引发进一步的争论,但它并不趋向真理,不能提供可检验的新奇见解,从而也就不会促使科学家们对描述现实的基本概念做实质性的修改。
强者科学家们*常用的策略,是直指当前科学知识的缺陷,指向科学目前尚无法解答因而被搁置的所有问题,但因为人类科学局限性的存在,这些问题往往正是那些也许永远无法*终回答的问题。宇宙到底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的宇宙是否只是无限多的宇宙中的一个?夸克和电子是否是由更小的粒子(更更小的粒子……)组成的呢?量子力学的真正意义何在?大部分问题所涉及的内涵只能进行反讽式的回答,正如文学批评家所熟知的那样。生物学也有大量自身无法解开的疙瘩:地球上的生命到底是怎样发生的?生命的起源及其随后的发展历史究竟具有怎样的必然性呢?
反讽科学的实践者享有一种“强者诗人”所无法企及的优势,即大众读者们对科学“革命”的渴望。经验科学的停滞,使得像我这样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天职的新闻工作者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去炒卖那些估计可能会超越量子力学、大爆炸理论或自然选择论的理论。无论如何,对于那些名副其实的新学科,像混沌与复杂性研究等领域,尽管自称优于牛顿、爱因斯坦和达尔文等僵化的还原主义理论,但它们之所以家喻户晓,与新闻界的炒作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罗杰?彭罗斯关于意识的观点,凭借新闻工作者(包括我自己)的帮助,赢得的注意远大于其所应得到的,而职业神经科学家中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反而少得可怜。
我的意思不是说反讽的科学没有任何价值,恰恰相反,就像伟大的艺术或哲学或文学批评一样,出色的反讽科学诱发我们去思索,使我们对宇宙的奥秘保持敬畏之心,但却无法达到其超越既有真理的初衷,并且,它肯定无法给予我们(事实上,它只能使我们背离)“终极答案”——能够一劳永逸地满足我们好奇心的强有力的真理。总而言之,科学本身注定了我们人类永远只能满足于不完全的真理。
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将用来考察当今人类正在实践着的科学(第二章考察哲学的问题),在*后的两章中讨论这样一种可能性(赞同这一观点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人数多得出奇),即人类总有一天能够创造出可超越自身的有限认识能力的智能机。关于这点,我所欣赏的设想是:智能机会把整个宇宙转变成一个巨大的、统一的信息加工网络,所有的物质都变成了意识。这一设想当然并不科学,只是一厢情愿的设想,但它仍然引发出一些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向来属于神学家):一架全能的超级计算机有什么作用?它会“想”些什么?我只能想象一种可能,它会试图解答“终极问题”(The Question),即潜藏在所有问题背后的那个问题,就像一个演员扮演一出戏剧中的所有角色一样:为什么一定要有些什么,而不能一无所有?或许,在这个“宇宙智慧”为终极问题寻找终极答案的努力中,能够发现知识的终极限度。
……
装 帧:平装
页 数:304
版 次:第1版
开 本:16开